來康平的外地人,稍有逗留便會發現一個奇怪而有趣的現象,一連走過幾個、十幾個村莊,它們的名字也許都無一例外叫窩堡。那些來康平鄉下搞農副產品收購的商販們,更會有這樣的莫名感覺,走入一個又一個莊子打問其名,得到的回答極為雷同,形成了一長串的排比式:李家窩堡――劉家窩堡――瀋陽窩堡――楊大保窩堡――韓達子窩堡……康平何以這麼多窩堡?它有誘人的故事嗎?康平人怎樣看待家鄉的名字?有必要來一番刨根問底的追索和考證嗎?如果讀者感興趣的話,我首先告訴大家:康平的重要文化歷史就是從這些窩堡開始奠基的。

一
從北方大都市瀋陽去康平,僅百多公里,高速小車只需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然有一關口成為必經之地,否則,雖然條條新路可抵康平,卻免不了會繞上半天一日,讓駕駛者和乘客苦不堪言。
必經之地為法庫門。法庫門對康平如此重要為外地他鄉之客頗生疑惑,不把法庫門與康平的淵源關係弄清楚,就難懂其中的奧妙。其實,法庫門是古代界定康平地理方位的一個關鍵性標誌。北出法庫門,柳條邊寨以外,那星羅棋布的大小村莊便都是康平的了。東以遼河為界,北至內蒙古沙丘高原為止,西以遼西丘陵阻隔為限,這一片土地,歷來為人們所褒貶不一。且看:「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有人說南北朝民歌中的詩句是描寫康平的。「一出法庫門,只見牛羊不見人」。一幅古代水草豐美,畜牧興旺的圖景,以稀少的人口,放牧管理着群群牛羊,拿現在的眼光看,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時髦典型。而接下來的一句是:一過法庫門,一半牲口一半人。這句順口溜兒,康平人就難於接受了。這分明是鄙視康平人,把人和牲口摻和在一起相提並論了嗎。因為這句話,康平人總是跟那些口有不敬的人打嘴仗,討說法,爭個是非清楚才肯罷。其實,康平土地的肥與瘠,康平人的荒昧與文明,不可能一句詩、一句順口溜兒所能概括的。
據考古工作者的地下發掘考證,康平地域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即有人類活動,青銅時期已有人類居住,至遼金時期,康平地域已有相當人口定居,有些繁盛景象了,而由於戰爭和蒙古諸部的侵擾擄掠,元末至清初200多年間,康平地區又陷入人煙稀少的荒蕪狀態,直至清朝中葉的鼎盛時期,村落才漸漸稠密起來。
這種滄桑之變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清王朝在北京定都後,對東北滿族屬地實行圈禁政策。滿清政府還算體恤民情,一想修幾千里的長城太勞費民力,就簡單些吧,西起山海關,經錦州北鎮再經法庫鎮北到開原威遠堡又折向丹東鳳凰城,劃好路線,挖塹壕培高四、五尺,阻斷車輛通行。為防止行人偷越,又在壕上密插柳條,待柳條成活,長成樹蔭,拿樹枝子於樹幹間穿插編別,成為一道杖子,一條密實的柳樹牆寨便形成了。一道柳條邊寨把康平拋在邊外,人家法庫、新民在邊里大搞開發耕種,幹得熱火朝天,康平地界則成為蒙古三王領地,寥若晨星的村落,守着王荒之地,過着半農半牧的生活。邊寨在法庫設一邊門,農牧人出入,蒙古貴族進京朝貢,必由邊門通過,由把守人員發放通行證件並接受檢查方可通過,一旦有人偷越牆寨,要受到嚴厲處罰。在漫長的封禁時期,康平成為蒙古沙漠以外的標準牧場。
到了清中葉乾隆、嘉慶時期,隨着清皇室政權的日益鞏固,滿蒙關係日益親密,朝廷回過頭來看,也沒什麼了不得的大事,防賊似的防着蒙民入內,也影響兄弟民族的感情,遂逐漸開禁,允許邊寨內外自由往來。政策放開,蒙古王公擁有大片屬地,開始招募流民墾荒。恰逢關內連年遭災,直隸、山東一帶廣大農民紛紛破產,大批農民被迫「闖關東」,湧入東北。那股熱潮比之今天內地人員趨向沿海要來得更為猛烈。試想現在人們向沿海涌動,是為了尋求更為富足優越的生活,而當年「闖關東」的人們是為了活命啊!那些推小車、挑擔的強壯漢子,擔筐里挑着孩子,腳後跟着女人,日夜兼程趕來,山海關外,到處可以落腳,但逃荒的人們還是相信前頭有更加肥沃的黑土地在等着他們。可是挑了一程又一程,能占腳的地方都有了人家,繼續向北,結果把擔子挑過了盛京,一咬牙又來到了法庫門,站在邊門寨牆向北一望,哇,好開闊的地方!只見晴朗朗的天空下,漫崗平川,沃野連綿,碧草齊腰,牛羊群群,只是少有開墾的熟土。闖關東的漢子們有的是力氣,還愁生荒種不出糧食,便一股腦地湧入這片荒蕪之地,尋找心儀的地方搭窩棚建房子,村落便漸漸形成了。
清朝歷史上,滿蒙通婚極為普遍,很多皇室公主下嫁於蒙古王公貴族的後裔。固倫雍穆公主出嫁時,邊外一塊上好的膏腴之地做為陪嫁劃給了她的名下。光有土地是不夠的,沒有人才也不能夠很好地開發和經營,於是做為陪嫁的一批人跟隨到這裡落戶來了,不過這些人不是普通的農人,都是些可以各操兵刃的手藝人,什麼木匠、鐵匠、石匠、瓦匠、皮匠、機匠、豆腐匠……行業多得是,統稱為七十二行匠人吧。他們的到來,為後來康平的開發和社會進步,無疑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們也沒有更多的文化知識,甚至很多人都是目不識丁,但他們手中有技能,所以格外受到青睞。
蒙古貴族也看好了康平這塊土地。他們一次次騎着草原駿馬在這裡兜圈,是看定了這塊土地的風水。北起科爾沁沙地的博王府縱韁奔馳,直到盛京瀋陽,出了沙漠再入遼河平原,一抹緩漫的平川地,只是在康平地界的南緣有一脈山水,王公們看好了這處唯一的山地做靈寢墓地,幾代王孫埋葬在這裡。功德無量的王爺們長眠在這裡,得需要相當數量的守墓人戶,於是又一撥蒙古姓氏的人群奉命遷來,守着陵旁,建村立戶。綜上這三種因素,使康平地域的人口驟增,村落很快遍布境內的角角落落。據地名考察統計,明末清初時,康平境內的村落還寥寥無幾,而截止清末,現在的665個村屯中,已出現了641個,近百年來,僅僅新增了24個,大部分形成於清中葉乾隆、嘉慶、道光三朝。
現在,我們要追索一下,來到康平的這些先民們,當時在為村子取名的時候,有沒有認真地動動腦子思考一下,召集全聚落戶族家長民主商討一下呢?現在看來,顯然是沒有這些程序的。你看那一個個村屯的名字,都是以姓氏打頭,尾綴一個屯、街、店、窩堡等等。很顯然,誰家是聚落的原始首戶,就以其姓氏命名,絕無二意。現在想來,當時,非但沒有民主研討,就連被命為村名的始建者本人也未想過起名的事情,張家屯、李家窩堡竟是被別人叫開來的。事情很簡單,挑着擔子闖入邊外的一家數口,在荒野里選准了位置,挖土培壕,構木架棚,再苫草抹泥,築成了簡陋居舍,名為窩棚。若戶主姓李,改日有另聚落的人來探視,回去便說,我去了李家窩棚,這個聚落地名就這樣叫來叫去,便形成了。多年以後,聚落髮展到幾十戶人家,李姓戶主才回過神兒來,這屯子原來是以我家姓氏命名的,我怎麼沒有在意呢……
康平地名有多種稱謂叫法,而以「窩堡」最為普遍。統計一下,全縣村莊叫「窩堡」的竟有248個之多,而叫「屯」的才只有45個。要考證這些叫法,人們多以為是一種隨意,並未覺出有什麼深層意義上的區別和不同。而通過考證便找出一些規律來了,有地理環境的、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
康平地貌大體上分為三種類型交錯相連,那麼以地貌命名就順理成章了。東部為遼河平原,遂有牤牛河、背河趙家、天鵝泡、泗河汀等近水地貌的名字出現;西南部為丘陵崗地,便有蓮花崗、鴨蛋山、狐狸溝、星星溝等山地特徵的名字;西部北部地靠內蒙古沙地,故有曲家坨子、潘家崗子的稱謂,還有相當數量的蒙語地名間插其間。二牛所口、沙金台、東西扎哈氣、西二喇嘛、五漢朝老等,據考都是蒙語的轉音。地理環境的不同而影響聚落的名字,這是很自然不過的事情,而「屯」和「窩堡」又有什麼區別嗎?首先說屯,它們在康平多分布於東南面靠近柳條邊一帶,或是大道經過的沿路一線。這些地方,既不是坡陡石多的山地,也不是低洼鹽鹼的甸子地,都是一色的平川漫崗的膏腴之地。屯即有軍隊或官方差人屯駐的意思,實際上,這一帶恰是跟隨公主陪嫁前來的匠作雜役之人聚居的地方。看來「屯」的起點就比其他的地方高了一籌。
諸多叫法中,「窩堡」是最為寒酸的了,窩堡是早先「窩棚」二字演變過來的,多為挑擔闖關東的遲到者,被統治者稱為流民的關內戶,肥沃之地豈敢奢望,看看好地方已被占盡,肩擔遠足,力已耗盡,撿個沙包鹼窪之地棲居下來。這些聚落的形成,無疑凝聚着祖先們逃荒遷徙過程中無限的艱辛、悽苦,甚至是血淚斑斑了。辛酸的窩棚在康平的文化歷史上極具代表性。過去,外地人評價康平,找出康平人許多缺點,落後、散漫、進取意識差等等,這些性格缺失,在那些寒酸的窩棚里找到了文化積澱的根源,那些窩棚就是昔日康平面貌最為典型的寫照。當然這都是古代的歷史,在那些窩棚里,子孫繁衍正旺的時候,康平還沒有建縣,一個稍大些的聚落只管它叫康家屯。直到1880年(清光緒6年),朝廷頒下詔書,批准劃邊牆以外、遼河以西的廣大地區建縣,轄區面積很廣,有歷史記載的區域面積為6100平方公里,連當時很有名氣的吉林省的鄭家屯、內蒙古的金寶屯當時都劃入了康平的版圖。於是,那些屯、窩堡等村落悉數為康平縣管轄。從此,康平才以縣一級的建制,統管一地,相延至今。
二
康平的「窩棚」演變為「窩堡」,想來是官方所為。康平建縣以後,那些縣令、縣丞們統攬民生、登記戶簿,在聚落名稱上肯定遇到了一些麻煩,其他稱謂倒還可以,這個「窩棚」卻極不順眼,官方用來也極不規範。窩棚一詞從字面上來看是個體指代,只能說它是一幢非常簡陋矮小的屋子,涵蓋不了整體居落,把「棚」換成「堡」就順理了。所以,後來在官方行政管理中,出現了「窩堡」二字。
窩堡的「堡」字,漢語拼音為bu,有人不加區別地用鋪(pu)的發音是不準確的。「堡」字在漢語字典里三個發音中,一為城堡(bao)的堡,二為三十里堡(pu)的堡,這二種解釋都不適用於遼北,唯有「補」(bu)的發音才更為切合,各類新老詞典,都把「堡(bu)子」一詞解釋為:圍有土牆的城鎮或鄉村,泛指村莊。也唯有這種解釋才與康平地域環境文化歷史最為妥帖。
康平的堡子都不是很大,百八十戶、四五十戶、二三十戶不等。方整的農家小院,以界牆相隔,戶戶相連構成了村落。小院和房屋,早年都是土的。土屋的牆壁有兩種築法,一是和泥壘垛,二是濕土打壓。泥垛的牆不能一次完成,並有中途坍倒的危險,故濕土打壓的辦法常被農人們採用。在村外選有粘性或鹼性的黃土,用畜力車拉來院內,在築牆的位置上,將長長的一副木板條,用立木夾起來,形成槽體,眾人揮鍬往裡填土,幾個壯漢早在板槽內踩實踏平,遂雙手高高舉起石蛋蛋,發狠力猛的向下砸去,石蛋的印痕如密密的針腳,一個接連着一個深深凹沉下去,幾位壯漢輪流下來,一層土夯實了,眾人再迅速填土,幾位壯漢再一次揮石密軋一遍,一板牆完成了,再上一副牆板,填土夯軋完成後,底下的一副牆板撤下返上來,輪番疊加上去,牆體一點點升高。為使屋牆結實耐久,每填層土要鋪撒一些短柴草,保持牆體的拉力,又在夯擊時不致使粘土粘住石蛋。一面牆夠了高度,轉向另一面,一副完好的四壁牆框立起來了。待改日選個吉祥時辰搭上樑檁,棚上屋頂,安上粗製門窗,一座土屋宣告竣工,主人便可搬入新居生活了。整個工程要耗費勞動工日百十左右,各項用料再加吃喝費用,是要積攢多年的。農戶把蓋房看作是人生最為艱難,也最為榮耀的頭等大事。哪家建屋動工這天,整個屯裡的勞動力全數前來幫工,幾掛畜力馬車也都趕來運土,眾人的吵嚷歡叫聲,石蛋落下的砰砰聲響,車馬往來嘈雜四起,真是熱鬧無比。特別是在高高的正在夯築的牆體上,那壯漢把石蛋高高舉過頭頂,渾身的肌肉擰成了紫銅色的疙瘩,一腔的氣力喊出一聲「嘿」!石蛋猛然擊落下來……那種記憶,在人們的腦海里,早已形成了一尊雕像,至今揮之不去。
房屋,簡單的結構,泥土築壘,歲年須精心泥抹,保其夏雨不漏,嚴冬避寒。早春,大地剛剛化開一層土皮,農戶人趁農閒開始搶挖鹼土,拉回院內,擔水和泥拌「羊攪」,三四個壯漢要一天時間才能抹完屋頂,四周牆壁還須一天,有下屋的人家還要增添工時。這項活計很苦重,湯湯水水的泥巴,要用鍬叉甩拋到高高的屋頂,又要手持抹板用力將泥巴擺平,抹個緻密光滑漂亮,一日下來,壯漢累得腰酸腿軟,腕肘麻木。農人諺語:造屋抹房,活見閻王。幾日的泥水髒苦,小屋煥然一新,主人臉上也煥發了喜氣。屋牆一層皮,為它罩上了新衣,主人臉面也光彩呀,好像娶了新婦一般,進出院門,一身輕鬆,勞作起來心情格外暢快。可是,從春到秋,大雨小雨不斷,幾場暴雨潑降下來,泥屋便凋顏鄙貌,頹然而無精打采的樣子,變得非常醜陋,又須來年一連幾日的勞苦了。
泥屋有火炕。火炕的大小,憑房子的面積而裁定。兩間房子僻一間做廚房,叫外屋,裡間為寢室,臨窗的南面就被一鋪火炕所占據了。若三間房子,仍作「口袋式」結構處理,就有了兩間寢室,火炕也繼而成為連二大炕。火炕供農家人休憩就寢之用,溫熱而持久,世世代代為莊稼人養育了一副鐵骨錚錚的好身板。特別是到了冬季,乏累一天後,平臥於烙熱的火炕,腰背四肢舒舒服服地漸入夢鄉,睡的熨貼而滿足,天明一覺醒來,渾身筋骨輕鬆無比,那種享受,是世居城內睡床的人無法想象的。
火炕為農家人生存所必需。世代生息於此地的土著人所沿襲下來的生活方式,都是經歷史驗證過的,必是有它無所替代的價值。從古至今,多少風俗文化習慣被改革、甚至取締,而火炕一直沿用下來,也許再過一個世紀仍會依然吧。
東北農家普遍居寢於火炕,而各地區的火炕又有質的不同。居於山區,採石料作炕,巨大片石作炕面,加厚泥,石料撤溫快,而厚泥炕面卻保存了熱溫。較早產磚的地方以磚作炕,稜角方整,便於操作,炕面也易於找平。而康平少山,用石短缺,紅磚生產則是較晚的事情。早年用泥土打坯作炕,便是康平的一大特色了,就地取材的泥土,康平總不會缺少。表土為黑土耕作層,往下挖去即為細膩的黃粘土質,遇雨水變作膠一樣的粘着,待晾曬乾透,便堅硬如石。
當年,在農家存放農具的屋子裡,於昏暗的光線下,不經意間,你也許會發現土牆的釘橛之上懸掛着一隻木製長方形框具,這便是製作土坯的模具了。打制土坯須避開雨季,一般在仲秋時節,雨水旺季漸漸淡去,秋日陽光仍很毒火,這便是最佳的時日了。現在回想起來,打坯是一項很好玩的工作,於村頭上選一帶靠近水源、土質上好的地段作坯場,家家擺開了架勢,搶時打制。先將黑土層挖掉,見到了黃土,翻撮成堆,擔水加鍘過的短柴草,開始用力攪拌。同樣和泥,卻要比鹼土抹房時費力得多。鹼土和泥是順滑的,而黃土是頑固透頂的那種粘着,沒有幾個回合的扒倒折騰是不會成形的。主人生怕「羊攪」與泥土不勻,挽了褲腿,赤腳入泥巴中一陣踩踏,再經翻扒,用鎬頭打膩一遍,坯泥總算柔合了。這期間,男人的做工總要有女人的指點。女人是憑廚上和面時的經驗來指導男人,並親自查驗一次泥胎的軟硬均勻,說一聲好啦!男人便放心地上泥。而脫制過程一般由男主人來做,女人與孩子們只作幫手,端泥巴,供沿水。有經驗的扠泥者,一扠子撮來,恰好是一塊坯子的用量。男主人擺好木模子,在草地將泥胎滾了又滾,成一欖圓形的泥蛋蛋,雙手捧入模里。木模四周先要撩潑少許沿水,以便提模時滑爽順利,然後雙手合拳在模里捶壓一遍,表面用手掌反覆抹膩,達到光滑,便輕鬆一提模框,一具完好的泥水坯胎便形成了。接下來留好間距,脫制下一個。一行一行的脫出來,一片不小的範圍擺滿了,過三五日,坯子佯幹了,便逐塊掀起,依次立於原地。酷似多米諾骨牌的情形。為防止其如骨牌那般連鎖傾倒,遂擺成「z」字形,塊塊相頂,每行便形成了一條浪線狀,煞是有趣好看。男主人欣賞了一陣子「骨牌」,很穩固,便帶着好心情回家去。
此時,小院裡的風景更加迷人。這時節,女人把家裡所有的被褥全部拆洗了,用漿麵漿好,正於小院內扯起長繩晾曬。秋日陽光好,是女人漿洗的好日子,一年的污濁只指望這個季節被浣洗乾淨,再重打漿面,漿揉一次。長繩上懸掛的里兒面兒,展示着諸多花色品種。月白、靛藍、墨青、麻花,間或也有現代技術印染的細紋大花被面、褥單。那些色彩,每年僅有一次的展示機會。晾曬前,在女人的催促下,男人要將院內一切畜禽糞便、柴屑塵埃打掃乾淨,一道風景拉扯出來,小院顯示出一派出奇的溫馨,一股平日少有的文明氣息瀰漫於村莊院落,讓莊稼人自己感嘆,小院總是這個樣子該有多好!
幾日過後,小村之內打破了一慣的寧靜,家家響起了棒槌聲,那聲聲脆響,把婦人憂鬱已久的心胸擊打得亮亮堂堂,農家的窘困憂愁似乎全然不再了。在翻轉錘石上的被面時,年輕的婦人見到了那床麻花被面,那是自己親手搖車紡線,供土著織匠織就的土布,拿到康平縣城街里的染坊,染成了心愛的麻花色。一直漿洗捶打了多年,時下雖有了現代印染,卻也捨不得丟下。這裡有她們的血汗,有她們對於堡子以外大千世界的追求和夢想,青春的意念早已織就於細密的布紋里了。
三
捋順一下康平的發展歷史,遠古的不必贅述,只從民眾建起窩堡,官方建縣開始,康平一步一步發展到今天,一定積澱了厚厚的文化土層。世人評說一個地方,能說出一些總體特徵來,大體上也是從文化角度,所以說,文化冠蓋的一個地區的面貌,是一個地方的形象。而地域文化是生活在此處的人來創造的,說一個地方首先就要評價這個地方的人。那麼外地人怎樣評價康平人呢?從各種信息來源上可歸列出以下詞語:老實、熱情、真誠、倔強、堅忍、僵化、懶散、接受新事物慢……可能還有許多,把這些評語歸納一下,既有褒也有貶,這是情理之中的,不過康平人諸多的個性中,值得炫耀的並不多,而其中有些突出的個性,就只有倔強、堅忍了。
時下小品盛行,老實的康平人也學會了調侃,而最為精彩的一段口頭小品便是:瀋陽人有什麼了不起?康平人哪點差?我們兩家的祖先當年是結伴闖關東來的,擔子挑到瀋陽,他們的祖先身體瘦弱挑不動了,只好歇腳落了戶,而我們的祖先,由於腰板硬朗,一鼓作氣多挑出200多里,在康平扎了根!若是我們的祖宗當年也耍熊,落腳瀋陽,如今我們也是響噹噹的城裡人啊!這種說法作為小品可能引來一些笑聲,但把它作為史實來考證,相信的人就不會更多了。不過評說起來,康平人性格堅忍倔強的一面還是世人公認的。
我的祖籍是山東壽光,曾祖父最早來闖關東,憑着一手織布手藝,在堡子里落戶,成為人人尊敬的硬漢。他去世時,我的父親才剛剛十幾歲,我們只見到他的墳頭排在最前位,他那闖關東的故事也只能是傳說,而本家族裡面有位八爺卻是我們從小陪着他在堡子里生活過來的,印象極深。中等個頭,敦實的身板,由於闖關東的年代較晚,滿口山東語音侉調,直到老去也未能改變過來。據他講闖關東的原因不是鬧災荒,是因為他給人家放牛,其中有一頭牤牛極不馴順,見人就頂撞,已傷了好幾個人。一日他在野外放牧時牤牛向他撞來,他年輕氣盛,手持粗棍,辟頭一棒打來,牛當場暈倒在地,他等過半晌也未醒來,怕是死掉了,窮困之家哪裡賠得起一頭壯牛,便丟下牛群跑了出來。當得知那頭牛最終緩醒過來了的時候,他已投奔康平,在叔父先期到來的滕家窩堡落腳了。八爺與堡子里的農人一樣,過着純樸堅忍的生活,日子也一步步富足起來,他的壽命很長,活到了94歲,前些年才去世。他看着新社會,領受着改革開放,還跨過了新世紀的門檻,他一生很知足了。然而讓人難於理解的是,他自十五六歲來堡子,竟一次老家也未回去過。他不想自己的故鄉?不想自己至近的族人?平時晚輩後生們也問過他,當時他只是長長地吁出一口氣:「嗨――」!表情木然,口中卻再也無語了。一個「嗨」把他一生一世的內心苦痛全都涵蓋在裡邊了。沒有寧死不回頭的倔強性格,能忍受得住思鄉的苦痛嗎?沒有堅持再堅持的忍受,作為拓荒的一代,別說一步步打造幸福生活,就是紮下根來也是很難的事。
再看那些最初命下村名的人戶,後來的命運更為舛錯。這些開荒占草時的名譽莊主們,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建戶立村,只擔了一個村莊的名號,由於創業早,生產積累豐厚些,成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在村屯堡子里,他們是倍受尊敬的,而土改時期一般都被劃了高成份,不是地主便是富農。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日子都不好過。於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產生了。小時候,我們從未對自己的出生地產生過驕傲,心裡上有了深深的烙印,對那些窩堡始終懷有一種鄙視,心裡總是疙疙瘩瘩,都在討厭自己的出生地--那些窩堡們。你看,你是張家窩堡的,張家正是人人喊打的地主;你是李家窩堡的,李家恰是被天天批鬥的富農,一個幾十上百戶的堡子,都是被時下整個社會厭惡的地主富農的姓氏所冠蓋着。再說,那些「窩堡」往後一綴,土裡土氣讓人難以揚眉挺胸。你看關里那些上了電影的杏花村、紅石峪多美,最損弄個趙家莊、馬家河子也比窩堡順氣。人們心裡憤憤不平了,決心要改一改。怎們改呢?改掉前面的姓氏便失掉了匡限,一群窩堡哪得區分,整體名字全都取消另改新的,那麼整個康平地方一片陌生,人們像到了一個怪異的他鄉,七姑八姨居於何處都難於找到了。不行,改不得,地主就地主,富農就富農吧。倒是有一個時期,傳統的村名在人們的口頭上被簡化了,辦法是一律把窩堡去掉,李家窩堡就叫李家,趙家窩堡就叫趙家。這樣一簡化,倒省事許多,卻也不倫不類。人民公社體制時期,我所在的生產小隊是滕家窩堡西隊,被簡化為滕西隊,本地人們明白是咋回事,而外地人聽來只是一頭霧水,我也感到了彆扭。少不更事,難免想法離譜,一次為市報寫的一篇報道中,把「滕西」改為「騰溪」,一經在報上登載出來,頗受人們的青睞。哦,奔騰的小溪,多麼歡快靈動的名字啊。連發稿的編輯都認定了這是個山區小村,泉水叮咚日夜流淌的一個所在,來信說非要親自來看一看,結果被我婉言拒絕了。看來一個地方名字的作用還真不小,不過引起歧義也夠麻煩的,改來改去人們覺得還是不改的好。說到底它就是一個地方的文字標號而已,經過世代的積澱,遂成為一種史傳文化。文化就像溫軟的水,經自己的耐性,可以把石頭磨洗圓潤光滑。而文化一旦形成,任何人為的政治力量都難於改變,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
「窩堡」二字終究沒能被省略掉,而那些名譽莊主們的後裔卻大都走掉了。土改乃至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那些地主富農們都要被當靶子,受盡了歧視,這是祖先們在荒野里立下首戶時所始料未及的。又批又斗的景況難於再熬下去,結果,他們選擇了再一次逃荒。他們都是棄掉親手建造的房屋,連鄰居也不敢打一聲招呼,背着行李卷,於夜深人靜時,默默告別老屋,偷偷上路的。想來好寒心,早年創業的功臣,此時他們的兒孫們為政治所迫,不得不告別地下的先祖,背井離鄉另尋出路去了。康平人的去向多是松花江以北,嫩江以東的廣大地區,當時叫北大荒,他們以盲流的身份,管自己的行動叫闖江東。早年那一撥是闖關東,現在又一撥闖江東,一個關東、一個江東,被逼無奈,步步向北啊!他們在那裡又一次像祖先來康平時那樣,搭棚立戶,拓荒墾植,開始新一輪的艱難創業。有一點不同的是,他們所建立的村落絕不叫窩堡。都起了一個漂亮的名字。有一個幾百戶的大村落,百分之五十是康平人,取了個頗有文化含量的名字叫聚賢屯。一個時代過去了,北大荒建成了米糧倉,而改革開放後,政治和緩了,時代變得寬容了,而那些逃荒的人家,卻絕少有遷回故地的。遊走北大荒的人們啊,秉承了八爺們的倔強性格,創業在哪裡,紮根在哪裡。祖上有句老話,他們記得牢:好馬不吃回頭草啊!
四
1992年12月,一份國務院的文件批轉下來,康平縣重新劃歸瀋陽市。看來就是一個規屬問題,而就我們所處的歷史時期而言,這是一個大事件,絕不亞於清光緒帝頒旨建縣時的歷史意義。
康平地方歷史悠久,命運多有跌宕。除早年亂投其主外,僅建縣後,地理沿革,行政區劃的變動就有16次之多,重要的動態隸屬變動有:1880年建縣時規昌圖府管轄;偽滿時期屬奉天省;1947年11月康平解放初始屬遼北省;1949年5月,遼北省撤銷,劃規遼西省(省會在錦州);1956年屬鐵嶺專區;1958年劃規瀋陽市;1968年重規鐵嶺專區,後屬鐵嶺市;1992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康平縣重新劃歸瀋陽市。時代的變遷、地理沿革的變動,現今法庫門外十公里左右一帶不再是康平的地盤,北面的鄭家屯、金寶屯一帶也不再屬於康平的版圖,還劃出了省區界。而行政區劃無論變了多少次,康平的上屬多為瀋陽和鐵嶺。
憑心而論,康平與鐵嶺地緣較近,守着遼河兩岸對望相居,同屬遼北文化圈,多年相處,感情不薄。趙本山一夜走紅,鐵嶺成為人人開心並嚮往的「大城市」,此時康平劃歸瀋陽,似乎與此無關了,而趙本山一干人馬在央視大台一亮相,侃一段小品,甩出一曲純腔小調,康平人僅為行政區劃的原因而無動於衷嗎?那秧歌、二人轉婉轉的唱腔,那含着遼北土語方言的小品,聽來就是康平地道的土特產品,怎麼咀嚼也是一個味道。
而瀋陽呢,康平與瀋陽的關係,幾次分離歸屬,淵源甚厚,只不過瀋陽後來發展的規模越來越大,成為北方大都市,以瀋陽為中心形成了都市文化,而康平依然固我地堅守着隅角里的純樸和傳統,與瀋陽多年若即若離的關係,首先在文化上有所分野,人們在心理上產生一定的差距,這是自然的。而一但重新劃歸瀋陽,依託大城市,康平的快速發展有了無限的前景。這是同根的兄弟又一次歸伙團聚,不管怎麼說,作為堂兄的瀋陽,時隔多個世紀,仍沒忘記康平,伸出手來拉小弟來了。只是歸伙那天,埋怨了幾句祖叔們當年的逞強,擔子多挑出200里想避開大地方,亂世求僻靜。今天逢上了盛世,一起聯手再創大業吧!
上個世紀90年代初,電視劇《少奇在東北》劇組,來康平拍攝外景,這讓康平人感到了極度興奮和好奇。眾人聚在縣招待所,圍堵追看特型演員郭法曾,而細細打問,人們的熱情一下子降溫了。為啥來康平?因為康平土房多,那些土裡土氣的窩堡,還有土裡土氣的房屋適合於劇情環境的需要。康平人知道了拍劇的緣由,頓感氣餒,好長時間情緒低迷而沮喪。時間僅僅推移十多年,而現在呢,哪個劇組再要來尋找七扭八歪的土房子,恐怕不太容易了。過去,康平土地鹽鹼含量特別重。起初,古人來康平,每到春季要掃鹼,凡有低洼處,便有白花花的鹼片,人們挑着擔子把含鹼最重的土皮屑一擔擔運回家裡,煎熬一氣,形成個大大的鹼坨子,把它叫做大鹼,用它來代替蘇打發麵食用。而田野里,鹽鹼重的地塊是不長苗的,為此,農人棄掉了好多土地。包產到戶後,土地越來越被農民看好,很多荒鹼地被開墾起來耕種。說來奇怪,農民翻一塊種一塊,塊塊都變為畝產千斤的上好良田,祖宗們即使從墳墓中醒來,萬萬也不敢相信,這就是他們開荒占草的地盤,哪裡還找得到稍有片量的荒草和鹼片,連溝溝汊汊都是綠森森的莊稼。看來,祖先們寄望的遍地良田的夢景終於實現了。土屋沒了,用於養護土屋的鹼地也隨之消失了,座座磚石結構的瓦房替代了古老的土屋,間或也有小樓豎起來,祖宗們用過的彎把犁成為文人們到處尋找收藏的民俗古物,四輪農田機車出入萬千農家,遍于田野耕爬。
名字還是祖先起的那些名字,窩堡卻不是那些窩堡的原貌了,幾代人口更迭,戶數增多了,土屋不見了,紅牆瓦舍,綠樹掩映。更讓人關心惦記的是,那些蜘蛛網一樣串連着一個窩堡又一個窩堡的土路,還那麼泥濘嗎?
康平的地名中有很多叫店的,蘭家店、李孤店、孫家店、候家店,考查者把它們串連起來,認定這是一條古道,盛京瀋陽通往蒙古王府的通道。道邊必有店家供旅人歇宿,後來以店聚起村落。村落形成了,名字亘古未改,而古道卻早已廢棄。改革開放後的康平,一條新興的203國道,從瀋陽始,穿越法庫北門,貫穿康平南北,向北伸向內蒙古、吉林,直至黑龍江的明水;彰桓線省道橫貫康平全境,連接東西兩條鐵路交通大動脈,還深入到遼東山區桓仁;新世紀的門檻跨越之後,鐵朝高速公路先行建成通車,從昌圖接近四平的幹道接入,橫貫康平全境,過阜新至朝陽,再入河北過承德直至北京。爾後沈康高速建成通車,繼而,直線向北延伸到鄭家屯、松原,直至大慶。看來康平交通很發達了。而康平的鄉下歷史上一直是泥濘着的,人行小路泥濘着,畜力木輪車、鐵車、膠輪大車碾軋過的大道仍然是泥濘的。邁過新世紀的門檻,剛剛疾走了幾步,康平鄉村的泥濘,一夜之間幾乎不再了。全國村村通油路項目,首先在康平開工試點,僅僅三年間,鄉村道路脫掉了泥濘,光光的柏油路,讓泥腿子農民洗去污濁,換上錚亮的皮鞋,象城裡人那樣,踏動腳步,欣賞自己腳後發出的脆響,很洋氣的感覺,很有神采。跨上新買來的摩托一圈圈很有興致地兜風,農田裡無須傳統笨拙的辛勞,青年農民到新落成的北方塑編城打工掙錢,成為上班族的工人。早晚閒暇時光到村裡的文化廣場裡去,散步、休憩和遊樂,有了城裡人逛公園的輕鬆愉悅。
在貧窮落後苦苦奮鬥的歲月,康平人曾有過惡毒的咒祖言行。由於地域環境的差異,當時康平看不到希望,尋不到出路,一致認為今人落到這步田地,先人是有責任的,首先歸咎於祖先。而後來康平人終於想通了,光埋怨祖先有用嗎?他們當年在這裡落戶容易嗎?今天的我們有沒有責任呢?祖先的使命是在這塊土地上紮下根來,我們的責任是如何建設好家鄉,不然兒孫後代不也會如此來埋怨咒罵我們嗎?
現在,康平鄉村建設有了今非昔比的變化。房舍、道路、村屯環境,也包括人們對於家鄉名字的坦然心理。那些窩堡造就了康平人不畏艱難、奮力開拓、打造全新生活的鐵漢精神,而這種精神如今已成為了康平人可貴的一筆文化遺產,他們要拼力守住這可愛的精神家園,這是他們發軔的根,當這塊古來一直落後的地方完全進入小康社會的時候,他們也忘不了深情地呼喚一聲:
哦,遙遠而可親可愛的窩堡……
2006年7月初稿
2007年11定稿
2017年結集再次增改校訂
作者簡介:王甸葆,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康平縣作家協會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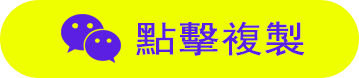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這個真的給我們很多幫助,特別是對愛情懵懂無知的年紀,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