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離開得悄無聲息,也沒帶什麼行李,聯繫方式通通換了,那麼大一個人,一眨眼卻了無痕蹤。
一
2002年的夏天,在小縣城的火車站,父親指着零售鋪里五花八門的小吃零嘴對我說:「隨便選些你喜歡的吧,等會在車上可沒晚飯吃的。」我懵懵懂懂應了,又興奮又忐忑,來回掂量才捏着兩包便宜的豆乾蹭到櫃檯前。
那年我七歲,身高將將在免票線邊緣試探,為了省錢,父親只買了一張硬座票,我們擠在一個狹小的位置上熬過十八個小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車,雖然擁擠不堪,人聲喧譁,還有各種食物香水和汗臭味混雜成的奇異味道,但對新事物的好奇暫且壓過了環境的惡劣和我心底的焦慮不安。

那焦慮不安來源於此次出行的目的——尋母。
兩個多月前,母親一聲不響離開了家,離開了我和父親。可說是尋母,我並不知道父親要到哪裡去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尋到。父親只是一言不發,鎮定自若撫摸着我的頭。
隔着小桌板,我們對面坐着兩個穿着打扮時髦的大姐姐。她們往桌上擺了各種各樣的食物,有我熟悉的也有我從未見過的,散發着誘人的味道。相比之下,我嘴裡的豆乾瞬間變得如同嚼蠟。
也許是我的眼神太過直勾,其中一個姐姐忽然笑着遞給我一個熱麵包——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叫「漢堡」,說送給我吃。得到父親的許可後,我小聲說「謝謝」,雙手如獲至寶一般接過。沒過多久,她們吃完飯後就離開了,說是要去臥鋪那邊休息。
往後的很多年,回憶起這個場景,我都不禁會想,那時在她們的眼裡,父親和我該是什麼樣子呢。
二
我的母親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那時家裡條件不好,夾在中間的,總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那個。可能正是因為這不尷不尬的位置,才激起了她年輕時的叛逆。
那樣的母親算是家裡的「異類」,她熱情勇敢,獨立果斷,嚮往外面自由寬廣的世界,有一顆躁動不安的心,卻偏偏生在不知名的小縣城裡,受各種陳規舊俗所束縛。
適逢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得正猛,學歷止步於高中的母親便順勢開起了服裝店。花花綠綠的新式衣服映襯着青春洋溢的少女,在總是蒙着一層灰的小縣城裡算是令人心馳神往的畫面,誰都願意去瞧一瞧看一看。
母親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邂逅了她的初戀。
可這段自主的戀情最終沒能得到雙方家長的支持,沒等到開花結實就被外力蠻橫地扼殺在土壤中。初戀未果和孤立無援給母親的心底種下了恨的引子,同時悄無聲息地張開一層薄膜,橫亘在她和家人之間。
後來經由親戚介紹,母親認識了父親,兩人磨合一段時間,迅速走到了結婚生子的階段。
父親是大家眼裡的老好人,沒脾氣,不沾煙酒,模樣過得去,有一份收入不高但穩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對母親死心塌地。
剛開始他們應該也是有過幸福的。我出生時正值盛夏,父親便借了輛板車,吭哧吭哧拉着半車的西瓜去醫院接母親,因懷孕必須忌嘴的母親總算吃上饞了一個夏天的西瓜。
父親最愛對我念叨,我兩三歲時,他和母親一起帶我看燈會,我騎在他脖子上趁他不注意尿了他滿肩。父親說這話時總是笑着,滿眼的眷念幾乎要化作一汪水溢出眼眶。
母親大概也是記得父親的好的,偶爾聽到這些過往瑣事時也會笑得溫柔。可是後來有些事情便逐漸開始扭曲錯位。
隨着我的出生,家裡的開銷越來越大,原本對於兩個人綽綽有餘的收入開始有些拮据。父親那點固定工資甚至還沒有母親的服裝店掙得多,關鍵是他本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毫無改變的動向。母親覺得父親沒出息,註定一生陷在小縣城裡,可她自己卻是不甘止步於此。
父親原本想闖出點名堂,可就是缺了些膽識和運氣,只好安於工廠,最大的愛好就是定期買兩張彩票,做做中五百萬一夜暴富的美夢。他每期必買一注數字,是我生日的彩票,期待能有某種命定奇蹟,然而奇蹟一直沒有降臨,他也不氣餒,仍是笑呵呵把那串數字當成信念一般堅持買。
另一邊,母親的兩個姐妹卻都嫁到了條件不錯的人家。原本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三個人突然一下子被拉開,起初最為領先的母親此刻卻掉到了最後,且落差越來越大。一向好強的母親開始焦躁不安,對於這樣知足常樂的父親,也自然是越發看不上眼。
他們開始爭吵,這些爭吵貫穿了我所能追溯到的整個童年時期。
確切的說,應該是母親單方面發脾氣,老實巴交的父親總是賠着笑臉,也不管到底是不是他的錯,只能一邊忍氣吞聲,一邊安撫母親那敏感易怒的神經。看到這樣「死皮賴臉」的父親,母親只會更加氣不打一處來。
他們吵得最厲害的一次,母親衝動之下提着菜刀,用刀背就往父親屁股上招呼。即使這樣,父親也只是無奈地躲閃竄逃,別說還手,就連嘴上也是沒有一句怨言。而那時邊上的我也看不清,只覺得惶恐無比,往地上一坐就是嚎啕大哭,以此希望他們能停下來。
即使這個時候他們的婚姻已然開始破裂,父親仍對母親存有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動她,挽回她。
三
為了修補日漸破裂的感情,父親獨自去了外地打工。
父親在工作上向來是個好手,為人又正直,吃苦耐勞,為此他的老東家還挽留過一陣。
那時母親已經關了服裝店,改去她姐夫新開的工廠里幫忙。相應的,即將上小學的我開始借宿在母親姐姐——也就是大姨媽家,由外公外婆負責照料,只有周末或者節假日時才會被母親接回去稍作團聚。
也許是距離產生美,也許是父親上交的收入變多,那段時間他們的關係有所緩和,偶爾一通電話也都是心平氣和甚至溫言軟語。
母親還親自帶我去看望過父親一次。
我們到達的時候,父親還在上工,身為技工的他竟和另外幾個身材健碩的工人一起搬運裝車的木材。後來我才知道,父親為了多掙點錢,除了本職工作,常常還會主動做一些按次數計報酬的體力活。
本是秋風蕭瑟的時節,他們只穿着單薄的T恤,有些乾脆光着上身,就算這樣,幾趟來回下來也都濕了鬢角、周身冒着騰騰的熱氣。幹完活,一個戴着帽子的人喊了父親的名字,遞給他一摞一元硬幣,大概也就二十枚的樣子,父親擦擦手,小心接過,回頭沖我們笑笑便將硬幣全部給了我。
我這才來得及好好打量父親,他黑了也瘦了,下巴上還有沒剃乾淨的胡茬,撫摸我臉頰的手掌上新添了不少硬繭。但父親的精神卻明顯很好,也許是高興母親和我的到來。
午休時,我們擠在父親的宿舍里閒話家常。說是宿舍,不過是搭在頂樓的一個小棚屋,屋內除了一張摺疊床、一個柜子,幾乎沒有別的東西。那光景母親看了也有些不忍,一面注視着父親一面拉着我的手告訴我:「爸爸在外面掙錢不容易,你一定要珍惜,要好好學習。」父親只是撓撓脖子,呵呵地笑。
那大概是留在我記憶里一家三口最後的溫馨情景。
後來因為一些變故,父親從外地回來,沒過多久,他們重新開始爭吵。那時我仍寄宿在大姨媽家裡,對父母之間急轉直下的關係不甚了解,還天真地以為自己馬上就不用再寄人籬下,可以回自己家,回到原來的生活。
誰知再也回不去了。
母親離家出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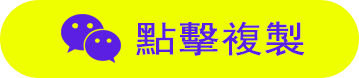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現代年輕人的情感問題很多,需要這樣的情感諮詢師,很專業
可以幫助複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