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時住在汽車站邊上,順着月台砌起的一道長紅磚牆把住宅區和火車軌道隔開起來。牆西邊變成一個小小三岔口,姥姥在三角的尖長上開過一家小商店,周邊胡同里的大人小孩都來購物聊閒天。寶梁緊挨着我家後院住,也來的最勤勞。
那時年齡小,空餘情況下多,一天有一大半時間我還坐着小商店中間的藤椅上看電視劇。寶梁不象他人一樣,每日朝九晚五工作,經常是早上日頭不斷上漲的九、十點鐘,悠悠閒閒地扯開全透明塑料門帘子走入來,腳掌下的黑色千層底踢嗒踢嗒的。
「叫舅爺!」
他年紀恰好卡在兩輩人中間,看到我奶奶就嬉皮笑臉地叫三姐。如果我奶奶沒有,他就要我的名字叫他舅爺。

「不叫!」
寶梁又說:「你叫不叫?不要我之後不許你打街機遊戲機。」
寶梁家裡有一個小霸王兒童學習機,我經常跑去他們家玩遊戲,回家了的情況下沾到一身他們家京巴狗的白毛。
「舅爺。」我細聲自言自語了一句。
「哎!這就對了,來,給舅爺把起子遞過。」說着他就駕輕就熟地從葡萄酒小箱子裡抽出來一瓶綠瑩瑩的燕京,接到起子「呲」的一聲撬開瓶蓋,翻過去看一下裡邊。
「讓你,臭小子。」他把瓶塞朝我扔回來。那時的燕京也有抽獎,有的瓶塞里會印上一毛或是兩毛的藍字。寶梁吹拂下頜咕咚咕咚地喝起來,外溢的葡萄酒會沿着他短而打卷的絡腮鬍子流下來少量來,黢黑的脖子上喉節一鼓一鼓的。
「今天有車票嗎?」我提心弔膽地問道。
寶梁不吭聲,低頭站立起來,手沿着腰部摸進很髒的超短褲屁兜,抽出來一張淡粉色的紙條,穩穩噹噹拍在玻璃櫃檯上。我在藤椅上跳起,把車票放到手內心細心看。這張車票的考慮站是三門峽,印着這一地名大全的車票我都沒有見過。
我顛回來倒以往擺布車票的情況下,寶梁就在邊上一邊看見電視機一邊喝酒,過一會兒說:「行了行了,快收吧,看上去不停了還。」
寶梁的謀生和汽車站相關,用他得話而言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汽車站就圍住列車轉」。他算一個半黃牛黨,自然都不全做這一,好多個火車車次的廢棄物和剩飯剩菜都歸他管。他去月台子上從不走正路,只是從紅磚牆上生生翻過去,隨後像走平衡木一樣在牆頭上閒庭信步一段兒,又活潑可愛又穩妥。
每日中午一點,寶梁固定不動要去站口上收垃圾倒車票,我坐着院子裡做作業的情況下,常常看到寶梁把幾硬包用黑色包裝袋裝着的物品從牆頭扔到地面上,傳出噗的一聲,颳起一片灰塵。他岔開腿坐着最高點,從袋子裡摸出來一盒擠扁的硬包玉蘭,抽出來一根叼在口中。他漸漸地把煙吸完,再翻盤跳下牆。跳下去以前他都會瞅我一眼,笑眯眯地喊一句「好好地做作業」,我甩他一個嘲諷,等再仰頭的情況下,他早已沒影兒了。
那一段時間電視上已經播《燕子李三》,我總感覺他類似有三分之二個李三那麼強大。
寶梁平常鬍子拉碴,不修邊幅,腳掌下帆布鞋拖地板的響聲令人煩心,可他答應我的車票從未跑過。有一回我們倆坐着小商店裡,我跟寶梁說我都沒有坐過列車,哪裡都沒來過。
「你之後變大就能乘火車到其他地區來到,沒準兒遠到要坐硬臥呢。」
我還在腦海中里想想想,我沒坐過列車,更不要說在火車上躺下來睡着了。
「你要想車票不?」寶梁嘬了口煙跟我說。
「哪些車票?」
「便是中國各省到咱這裡的車票啊。咱離北京市近,車多,到的地區也多。你如果要想,我還在站在接到車票就讓你存着。」
我用勁地點了點頭。從今以後,寶梁每周都幫我一張車票,我一張張都塞入相冊圖片裡,放到照片的反面。就是這樣堅持不懈了一年多,一個相冊圖片都用完後,這一件事情也從未斷過。
直至有一天,有些人隔着銀行櫃檯探過身來,好像傳輸商業秘密一樣對奶奶說了兩三句,儘管響聲不大但也充足想聽清晰了。他們說,寶梁的媳婦兒大萍和老二好啦。
老二住在巷子裡面,又高又大的軀體像一隻緘默的白熊。他爸踏踏實實在機務段上工作中了一輩子,老二追上接任的小尾巴,每日在地鐵站上搖搖晃晃。寶梁往往能在地鐵站上混,全拜當時老二詳細介紹,把幾個軟中華送去,才商議好每月的份錢。可在別人來看,她們2個不很熟識,也就是一起抽根煙的情分。每一次在小商店裡碰到,寶梁一直熟絡地抽出來一根煙說,來一根?老二搖搖頭,抽出來自身的一根拿給寶梁說:「還是來我這個吧。」
那周我坐着小商店,內心一直敲鼓,期待寶梁能仍舊來幫我送車票,也期待他不必和老二碰到。溜溜等了五天,到禮拜日的早上我還早已失落了。夏季的下午炎熱且喧鬧,我百無聊賴地喝着碳酸飲料,感覺啥都沒有含意。
寶梁來啦。這次他沒讓我的名字叫他舅爺,只是立即扯開冷櫃取出一瓶冰飲葡萄酒,把瓶塞邊緣放到窗戶上拍開,仰脖兒喝起來。忽然看到一直期待的人要我既高興又焦慮不安,由於我早已知道大萍外遇的事兒。我儘可能讓自身主要表現得釋放壓力,不許他發覺一切異常。一樣,由於獲知了密秘,我過意不去積極向他問及車票的事兒。在平常,我急不可耐的模樣都要被寶梁裝作看不上。
「不必車票了?」寶梁學會放下玻璃瓶盯住我。
「要啊。」我趕快說,「有誰知道你這禮拜來的很晚,還以為你沒來啦呢。」
「來,回來,讓你看一下這一。」他門把伸過來。
我盯住那張票,是以武漢市發班的,終點確是北京市。我非常少接到終點並不是當地的車票,這讓我很開心。
「這是誰的票?他為什麼沒有坐到北京呢?」我詢問道。
「或許他買不到到這裡的票,或許是他忽然改想法了,有誰知道呢。」寶梁說。
我將車票展開放到玻璃櫃檯上邊,轉頭看一下牆壁的地形圖,盤算着從武漢到北京多遠。
在哪以後,老二消失,寶梁出現的頻次也越來越少了,可每星期依然會來幫我送車票。車票愈來愈多,我惦記着如果有一天都搜集完後會怎麼樣。一次我詢問寶梁近期在幹什麼,他抓了抓又亂又黑的秀髮,還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樣說,賺錢呢。
一天我經過他大門口,看到大萍坐着巷子公共自來水龍頭前,把空罐一個個從黑色包裝袋裡抓出去,放到水龍頭下沖一下,再注滿水,如同生產流水線上的職工一樣機械設備且高效率。大萍僅用一個小時就注滿一大袋玻璃瓶。
「你這不要緊?你看看這瓶塞都沒擰死,一看就要人開啟過。」我詢問。
「我也賣五毛啊。」寶梁立在牆頭,還是笑眯眯的。
「別人一塊買的是純淨水,你這五毛是飲用水啊。」
「哪裡有哪些純淨水,全是胡說八道。更何況我也賣五毛錢。」
大萍把放滿純淨水的黑色包裝袋用勁甩上來,寶梁一低頭妥妥抓住,要了解牆頭的總寬僅有一搾長。兩人心有靈犀十足,如同啥事都沒產生過。他一件事喊一聲「離開了」,就跳來到月台子上。
寶梁的吊帶背心長期維持一種不乾不淨的感觀,人也越來越更黑了——想來是在站口上長期的奔忙造成 。我覺得他如今那樣匆匆忙忙,已不像以前那般不着調,每日掙夠就來店內喝酒閒胡扯,有一種說不出的覺得。他有多一點錢能給大萍買倆件新衣服雖然是好,可那時候的我還是期待他能每天玩世不恭地與我玩笑,讓我將開瓶器丟給他。
沒多久,寶梁從牆壁摔了出來,小腿斷了,裹上的熟石膏使他頭一次越來越舉步維艱,像只斷翅的小鳥。平常雄健的寶梁迅速就融入了雙拐行走的方式,因此重返回每日搖搖晃晃來小商店的生活。醫師不許飲酒,他就用花生仁來替代。我詢問他難道說並不是越吃花生米越想喝酒嗎,他不置可否,僅僅一顆顆放入口中。
胡同里除開氣體也有流言蜚語,有些人說寶梁是由於吃不消大萍外遇,想不通從牆壁跳下去。實際上因為我感覺怪異,客觀性說寶梁的動作迅速能夠算是上半隻小猴子,這些年我乃至沒有見他腳掌下打了一次滑。
一些事兒,除非是你有意而為,要不然是不太可能產生的。我認為這即使一件。我自然不容易問個到底,寶梁想要坐下來漸漸地吃花生米便是好的,唯一不太好的是,他無法幫我帶車票回家了。
吃了一袋花生仁,寶梁抹抹手。我還在看武俠電視劇,他忽然說話了。
「哎,這夏季打石膏真不舒服,發癢的不好,好想把它破開。」說着他把一條硬實的白腿漸漸地搭到銀行櫃檯上。
「你了解我怎麼掉下去的嗎?」寶梁忽然積極跟我說。
「是怎麼回事?」
「我跟你說,那一天我還在站口上賣水,是我自身灌的這些水,我以前都跟那幫臭小子打過招乎的,酒煙都送了,有誰知道忽然來啦好多個大蓋帽朝我跑。裝水的竹籃讓她們踹飛走了,我覺得這幾個人並不是善茬,就趕快回去跑。剛翻出牆頭上,她們好多個就追了回來。我特麼腳底一軟就摔了出來。哎,點背。」
「那麼你之後小心點哦。」我寬慰他道。
「這段時間沒發給你帶車票了,回首補充你。」
「恩。」我也不知道他為何忽然積極與我講這種,只能開過一瓶北冰洋給他們。
夏季還未完畢,老二在消失了好長時間以後出現,按照慣例買來一包銀鑽,外出坐着小商店大門口的棋牌桌前邊替手。棋盤是開裂的木材,粗字上的綠紅漆料都被撫摩沒了。一次,后街哪個手勁十足的大胖子立即把「炮」給摔成兩半。老二的香灰掉在旗盤上一動不動,我小,不太懂,僅僅感覺低沉,不象他人每一次落址都帶著洪亮的「操」。
看棋的群體一陣奔涌隨後分離,是寶梁來啦。他扛起一根拐指向旗盤問另一個人:「你這車是否沒軲轆?」如同四大惡人里的段延慶一樣。
「起來起來起來,快一點。」寶梁連笑帶唬,老頭悻悻地站到一邊。大家都了解他混不吝。
兩人零距離坐下來,下手越來越迅速。寶梁每下一個子,都高高的抬起重重的拍下,震得香灰向小螞蟻一樣翻轉。十多分鐘以往,老二的元老忙於閃避,一個炮沒有針對性和目的性地行走,能看出去大約是寶梁要獲勝。
寶梁按住最後一個子的另外抬起頭,高喊了一聲「操你媽的」,臉部的小表情不太好描述。一圈人愣住了,不清楚這句話是否丟給誰的。
幾秒鐘的緘默,老二禁不住,一下撲了上去。
打架鬥毆在這裡片胡同里是平常的事兒,不平時的是貼在牆壁的拆遷通告。由於汽車站要推翻重蓋,住宅區必須轉移,以前看上去好像要始終維持下去的生活被一瞬間擺脫。群體如猢猻散去,來買葡萄酒和洗髮香波的人都少了。有一天我在這兒外出去上學,放學後立即返回了新房子。乃至沒有一個詳細的道別,而因為我沒有再碰到她們當中的所有人。
一次和姥姥閒聊,從一個剛過世的舊隔壁鄰居聊得了寶梁。姥姥嘆了一口氣,說:「寶梁不易。」
我沒講話,等待姥姥再次說下來。伴隨着我年紀的提高,大量的事兒能夠被討論。
「寶梁的媳婦兒,大萍,你是否還記得?她跟胡同里的老二好過。寶梁承攬的那好多個火車車次,每日中午一點就剛開始到站,晚一點也但是二三十分鐘。那一天不清楚怎麼啦,有一趟車一直晚一點待定,這類事情罕見,寶梁就提前回家,結果開門看到兩人躺在一塊。那時候也沒動手能力,僅僅大萍一直哭,哭得前院子都聽得一清二楚。
「寶梁在站口上愈來愈閉氣,不干又不好,只有靠着。你永遠不知道,有些人說寶梁從牆壁翻下來摔斷腳,便是老二叫人找的茬。也有人說成他自己跳的。寶梁這臭小子,平常着三不着兩,實際上挺可靠的。」
我講:「對,可大萍也是為什麼呢。」
「不清楚。也有人說成老二要斷寶梁的發財路分包給他人,大萍才同意的。可我覺得不會,這類事兒誰會往外說?總的來說,你覺得倒票這工作輕省呢?每日風輕輕吹日曬的。也有他收垃圾和剩飯剩菜,真挺苦的。產生這類事兒,勸都不太好勸。」姥姥又嘆了一口氣,搓着兩手慢悠悠地感慨起生活的艱辛。
寶梁和大萍在拆遷之初很早搬離,聽聞現在在遠郊區養殖養得如火如荼。這是一個平常人對自身生活的短暫性無法控制並最後重歸正規的小故事,倘若並不是姥姥提到,我都要忘記了,更不容易補齊不明的一部分。
這件事情一件事較大 的危害,是寶梁已不幫我送火車票。在哪以後,我迅速就缺失了這一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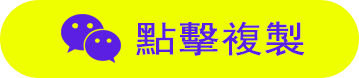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兩個人的感情往往都是當局者迷,找人開導一下就豁然開朗了
可以幫助複合嗎?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