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通訊員 樊金鳳
黎紫書近影。
6月26日19點,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等主辦的「一個盲女與一座馬來小城的故事——黎紫書《流俗地》新書發布會」在多個平台同步直播,當代著名作家王安憶、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浙江大學教授翟業軍,以及《流俗地》作者、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圍繞長篇小說《流俗地》,以及日常生活與精神向度等問題,展開了深入且真誠地討論。本次發布會由翟業軍主持。
黎紫書是馬來西亞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出版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微型小說集以及散文集等著作十餘部。

自1995年以來,多次獲得花蹤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獎項,也曾獲大馬優秀青年作家獎、雲里風年度優秀作家獎、南洋華文文學獎等。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獲第四屆紅樓夢長篇小說獎評審團獎。
近日,黎紫書長篇新作《流俗地》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甫一問世就備受關注,王德威、王安憶作序推薦,榮獲《亞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說,被譽為華語文學的驚喜收穫。
《流俗地》以馬來西亞錫都,被居民喊作「樓上樓」的小社會拉開序幕,講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務俗事。
主人公銀霞生來是盲女,她聰慧、敏感,亦懂得洞察人心,她既願意在家編織籮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她學象棋、上盲校,在生來的困頓里劈開了一片天。在盲校里,她學會用盲文寫信,也擁有了炙熱的愛情,一切看似向着美好的方向進行,殊不知黑暗已經降臨。
小說以跳接時空的敘事手法,為各個角色穿針引線,每一短篇看似獨立卻又連續,這些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里載浮載沉。他們擁有短暫歡樂,卻都像電光石火,剎那間便走到時間盡頭。
【流俗?這並不是一個貶義詞】
新書發布會的直播過程中,出現一個有趣的插曲:
一隻貓的聲音在直播間時常響起,有讀者留言「是黎紫書家的橘貓在叫嗎?」活動最後,黎紫書大方叫來橘貓與讀者「見面」。
這個場景和《流俗地》結尾「普乃」的出現形成了某種呼應,「有一隻貓從稍微敞開的窗戶跳了進來。銀霞聽到它的身體鑽過鐵花的空隙,落地時踩着什麼,發出細微聲響。她心裡一緊,眼前黮漶的黑暗忽然凝聚起來,變得厚實無比,似能反彈出回聲。『普乃?』她睜開眼睛。房裡先是一片寂靜,然後那貓說——喵嗚。」
小說的名字取得怪,叫《流俗地》。「流俗」不是含貶義麼?「俗」字尤其可厭,怎麼拿來當小說的名字?
黎紫書說,「流俗」於我,於這小說本身,並不是個貶義詞。
「我想到的是《紅樓夢》那樣的小說。拿《紅樓夢》來說自然是過於托大了,曹雪芹這小說裡頭哪怕一個丫鬟都比《流俗地》裡任何一個人物風雅而有逸趣。可我既然要着墨於流俗之地,自然追求的不是風雅,而是「風俗」;就如《漢書》上說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
黎紫書又說,「說好一個故事」,並不同於「說一個好故事」。
《流俗地》的主要人物多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小說里的錫都歷經數十年變化,其中裝載的正是黎紫書在馬來西亞的歲月。
「那裡頭寫的是我這一輩馬華人的經歷。因為是『一輩人』,小說里的人物很多,也必然充斥了各種事情和頭緒。早在很久以前,很可能始自我少年時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就很為小說中的群眾神往,無論是金庸筆下的天地會、紅花會諸多當家或明教教眾,抑或是古典小說如《水滸傳》裡的梁山好漢,甚至是《三國演義》中的群英,人物雲集,各具形貌風采,令人着迷不已。自我寫作以後,便時時幻想着自己以後也要這麼寫的——寫一部有很多人,有許多聲音,如同眾聲大合唱般的小說。」對於小說中的人物們,黎紫書說。
「既然心底埋着這樣一個想望,《流俗地》的醞釀和產生就成了無可避免之事。我一直都在等待人生中適當的時機,等自己有了足夠的見識和積累,並且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有了足夠的自信,可以向年輕時的夢想回身致意。」
這正是《流俗地》的醞釀過程。
她說,「我們這些在境外寫小說的人,總說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疏離,文明社會,特別是在城市裡的人性壓抑,加上大多數人的生活高度相仿,因而故事匱乏,更別說『好故事』了。我沒有費心去搜索好故事,也不去搜挖或創造非凡的人物,而是決心要往另一個方向走——把一群平凡不過的人放在一起,說他們最平凡的,可能也是庸俗的人生故事。這樣的故事本質上必然樸實無華,不會有多少意料之外的轉折與驚喜。它肯定缺乏戲劇性,也不具備『好故事』的特質和要素,但一個好的小說家,自該有說故事的能耐,可以調動技巧與文采,將『平平無奇』的故事說得引人入勝,讓人讀得欲罷不能,甚至讀後回味再三,不能自已。」
【它的溫暖,來自它顯示出的民間社會的力量】
王安憶對《流俗地》的高度評價,也引起了文學圈的廣泛關注。
王安憶說自己很早就開始閱讀馬來西亞作家的作品,她一直很看好黎紫書的小說創作,黎紫書獲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她也曾多次擔任評委。
關於《流俗地》的閱讀體驗,王安憶用了「順暢」「誠懇」「感動」幾個詞,「我沒有想到閱讀那麼順暢,能夠那麼影響我的閱讀情緒。這個故事首先非常飽滿,還有就是很完整。不僅是對海外的作者,對馬來西亞作者,對我們大陸作者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黎紫書那麼誠實地寫作,敘事的邏輯、現實、生活狀態的描寫都是那麼誠懇,而且有趣味,很感動。」
關於小說的語言,王安憶認為,馬來西亞作家的語言非常乾淨,因為他們從五四白話文的傳統過來,沒有受到太多現實的干擾,保持從新文學過來的一個很好的狀態,而黎紫書在使用語言時尤其自省,《流俗地》是一部非常紮實的長篇小說。
陳思和也是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的多屆評委,他對黎紫書的創作一直很關注,坦言讀《告別的年代》時做了很厚的筆記,這一部長篇《流俗地》非常成熟,對於整個馬華文學都有很大的促進。
陳思和主要從民間的概念剖析這部小說,他在這部小說的敘述中看到一個民間的社會,這個民間社會跟國族世界是不一樣的,它有自己認知世界的方式,但是它往往是被遮蔽的,作者選擇讓盲人銀霞去洞察,是非常好的角度。裡面的時間敘事很有意思,通過銀霞和細輝兩個人雙重不斷地回憶交錯,敘述這個故事,用一種民間對社會的感知,用黑暗世界對社會的感知的方式來敘述,很有新鮮感。
小說的最後,銀霞和顧老師在電梯黑暗時,銀霞說了一句話,「歡迎你來到我的世界。」
陳思和從這句話讀出一種民間的力量,「在這個民間社會中,最後不是顧老師給她光、拯救她、讓她擺脫黑暗的民間世界,而是她把顧老師吸引到黑暗的世界中去。這充分顯示出一種民間的力量。一直以來寫底層、寫平民的作品,往往包含一種悲天憫人,把平民寫得沒有出路、需要拯救。但是好的小說,即便寫生活在底層的苦難、寫既沒有知識也沒有力量的人們,在他們的故事當中仍然充滿了勇氣、充滿了力量。這部小說也是這樣,它的溫暖便來自它顯示出了民間社會的力量。」
翟業軍則是在小說關於愛的書寫上看到普通人的力量,「其實我更看重的是一種愛,執迷不悟的愛,鬼使神差的愛,不計較後果得失的愛,這種愛是一種弗洛伊德式的趨利,把愛的人趨向崇拜之利,執迷不悟地愛的人,身上散發出來一種崇高之美。蕙蘭、春分,包括葉公,他們都是如此卑微的人,他們根本不可能懂得愛,但他們就是憑着一種蠻憨的原力,生命的原力,沒有目的地愛。愛讓他們稀里糊塗、模模糊糊的生命有了硬的一面,有了鋼的一面,就像一個人有了骨頭一樣,於是他們就是人,他們就有了人氣。」
關於《流俗地》這本書,黎紫書坦言它與馬華文學向來的那種寫法——特別激烈、特別現代主義、後現代的寫法,不一樣,「我心目中的《流俗地》是這麼一部小說,它不是大眾化的類型小說,而是嚴肅的文學作品,但必須精彩,好看,能讓人享受到閱讀長篇小說該有的樂趣。我希望它是雅俗共賞的,是每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甚至每一個能看懂中文的人都能讀懂,都願意讀的一部小說。」
黎紫書近影。
【它讓我們看到生活的本相】
《流俗地》是黎紫書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相比較上一部《告別的年代》,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認為,《告別的年代》更注重小說技巧,新作回歸到寫實主義,顯示出作者更多的自信。
陳思和也有相似的評價,「我覺得《告別的年代》的力氣更多是花在敘事上,整個敘事非常精彩,但同時也是非常密集、非常厚重。如果說《告別的年代》重要的看點在敘事,《流俗地》重要的看點在一種氣象,這是很有氣象的一部小說,用比較抽象的說法就是很大氣,它的內容沒有《告別的年代》那麼複雜,但是這個故事發展當中有很多空白,就像中國傳統留白,讀起來有很多思考的餘地,很多迴響,所以我覺得紫書這部小說寫得更好更成熟。」
談到《流俗地》在「馬華文學」中的獨特性,王安憶認為,馬來西亞華人作家在寫作上吸收了更多現代主義的寫法,理論的、思辨的東西多,相比較而言,《流俗地》回歸到寫實主義,能夠發現一些日常生活的趣味,「我比較重視日常生活的美學。比如紫書生活的地方叫怡保,我就談談我對怡保的印象。有一天傍晚,在怡保的一座中國廟裡,有一名男子,大概四十來歲,穿着寬鬆的短褲,上衣好像連扣子都沒扣,穿了一雙拖鞋,走進廟裡,很快跪下來磕頭。我頓時非常感動,覺得這個地方充滿了故事,可是我進入不了,它跟我隔了一層。而這些故事在《流俗地》中遍地皆是,它不是經過總結、充滿理論和思辨、得出結論之後才告訴我的,它直接讓我們看到生活的本相。我個人覺得,好的小說還是要有一個常態的外部。」
「我預感到紫書這本書會開拓一個新的局面,馬來西亞作者會有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領域,就是他們開始把家國情懷、語言和在地語言的衝突等等,納入到日常生活的環境裡。有什麼比這更重要呢?他們在這麼複雜的環境裡度過,有那麼多豐富的故事可以寫。」王安憶對《流俗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翟業軍認為《流俗地》和其他「馬華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是,黎紫書不是就華人寫華人,而是描寫了一個五方雜處的世界。
對此,黎紫書回應,如果說我的作品有一些特別之處,可能是因為我和此前的一些作者有着不同的生活經驗,「我和他們對於馬來西亞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想法和感情是不同的,我不具備那麼強大的批判性,反而有一種和解的意識。在這裡生活五十年以後,我與馬來人、印度人相處很好,我和兩家馬來人整天討論怎樣餵養後巷的野貓。我決定忠於自己,誠誠懇懇寫一部我眼中、我心中的馬華文學長篇小說。」
黎紫書坦言,「馬華文學」的問題就是種類太少了。大家每次提到,就會想到殘暴的、野性的、血淋淋的、一整日都在下雨、人物都不怎麼看得見的小說,「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豐富馬華文學的種類,寫一些讓人物看得見的小說。」
【凡俗的人生里,那些無法被命名的東西】
作家如何把一個看似「平平無奇」的世俗故事說得引人入勝,讓人享受到閱讀長篇小說的樂趣?部分作家採用了寫實主義的方法。活動現場,關於寫實主義,陳思和談到了日常生活與精神向度的問題,這個話題引起了嘉賓們的熱烈討論。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因為剛才談到了這部小說的寫實主義問題。其實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寫實主義容易閱讀,而且它所講述的故事、生活都相對真實;但另一方面,寫實主義往往會走向庸俗社會學,講吃喝拉撒,講日常生活,講小人小事,講所謂苦難,而這種苦難是沒有精神性的。我認為對於長篇小說,精神性是第一位的,沒有精神就沒有好的長篇小說。《流俗地》雖然是寫實的,但它背後有非寫實的、精神性的因素在提升它,使它顯示出開闊的境界。」
黎紫書同意陳思和的觀點,她說,「我自己也覺得,可能沒有辦法在長篇小說中寫出驚人、曲折的故事,我知道我要寫的就是一群平凡不過的人和他們凡俗不過的人生。要把這樣的平凡小事寫得好看,當然不能只是用寫實手法寫一群人怎麼生活、怎麼吃飯、怎麼和朋友相處。這樣不僅庸俗,也不是我心中的『好看』。『好看』必須加入一些精神上的向度,在一群人怎樣生活的表象底下,還要有一些精神層面的東西可以打動讀者,這樣小說才不只是流水賬。」
王安憶補充道,「我覺得不能把庸俗怪到寫實主義上。小說的庸俗,絕對不是寫實的罪過,而跟精神有關係,跟人的精神利益有關係。我強調日常生活的美學,並不是說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義的,我不會把所有事情都納入我的寫作。因為思想是有限的,在我看來,小說就是傳達無法用思想和概念命名的東西,我們寫小說要表達的東西一定是在別的領域裡面沒有命名的東西。否則的話,我們何必再寫小說?這種東西只可能是生活提供給我們的。現在出現了一種趨勢,就是人們大量閱讀非虛構作品,因為非虛構中會出現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尤其是我們的思想和概念不能歸納的東西。」
【搶先讀】
《流俗地》節選
奀(ēn)仔之死
銀霞打來電話的時候,細輝正在便利店裡忙活,單膝跪在地上整理和補充着貨架上的飲料。他開的這家小鋪在鬧市,位置好,顧客多是附近各中小型酒店的住客,來買些冷飲、香煙和零食;左右十餘家按摩店的女工也經常三三兩兩來幫襯,多是給電話卡充值,或純粹只是出來走這一路,曬曬太陽,喘喘氣。深夜裡來的則是嫖客和妓女人妖之流,以及開夜車的貨車和德士司機等等,買幾罐紅牛,兩包香煙,散裝保險套或小支裝的潤滑液。這幾天假日,許多人到錫都來遊覽,周邊的酒店客滿,他店裡的生意比平日更好一些。嬋娟坐在櫃檯那裡,一邊收錢找贖,一邊騰出眼睛來盯緊對面牆上掛的防盜鏡。
細輝偶爾也會抬起頭,在那鑊底般的凸面鏡里與嬋娟的目光相遇。她的目光無感,仿佛他是鬼,她是看不見的。
「聽好,剛才我接到一通電話,打來召德士。」銀霞壓沉了聲音,聽起來像是在說什麼秘密。
細輝已經許久沒接過銀霞的電話了。她的聲音依然清脆,像電台主持人說話似的,每個字聽來都叮叮咚咚,如同屋檐掉下來的水珠,墜下時成冰,一顆一顆敲落在鐵盆子裡。「我認得出來那聲音,是你哥哥!」
細輝剛把一瓶礦泉水放到架子上,手便像被那瓶子粘住,沒挪下來。「你哥哥!」多久沒人對他這麼提起過了。偶爾他與都門的嫂子通電話,連她也極少這麼提起。說不清究竟是因為忌諱抑或是尷尬,真要提起來,她會說「孩子們的爸」。仿佛她跟大輝最後只剩下那一點關係。孩子是大輝撒下的種,那是他撇不掉的。
「怎麼可能?」細輝不期然也壓低聲線。
「我敢肯定!是大輝!」銀霞說得金石鏗鏘,細輝聽得耳朵嗡嗡作響。
「後來去載他的司機回報說,那是個中年男人,腿長,鼻子高,鳳眼。你說那是不是你哥呢?」
細輝愣在那兒,腦里的相冊翻了翻,看到大輝在不同時期的相貌。他的哥哥確實長得挺拔俊俏,以前大家都驚嘆過的,怎麼像他們的父母那麼矮小黝黑的一對,父親還被叫作「奀仔」呢,居然會生出來這麼一個白臉的長腿男孩。親友中有些口沒遮攔的,譬如銀霞的父親老古,多少次戲謔地說一定是醫院擺烏龍,抱錯孩子了。
「可那只是口述,又不是照片。很難說啊。」細輝沉吟片刻,仍然覺得這不靠譜,那已經是個消失了的人。
「你不相信我?我就聽出來是他!」銀霞越說越急,像在咬牙切齒,「不會錯!」
細輝與銀霞一起長大,曉得她的本事,也知道她的性子。他不想與她爭,口氣便軟了。
「今晚我給大嫂打個電話,打聽一下,看她那邊有沒有什麼消息。」
是呀,銀霞從小就這個性,倔,要強。正因為這樣,儘管天生殘缺,她卻不樂意像別的殘障人一樣,待在家裡接零活,做散工。以前他們住在近打河畔,就在舊街場一隅,鄰近小印度和壩羅華文小學,有一座組屋,樓高二十層,曾經是城中最高的建築物,被居民和周外圍的人喊作樓上樓。銀霞家住七樓,她母親讓她學着用尼龍繩織網,拿來給土產商裝柚子。因而她家客廳像個小型工廠,長年囤放着一捆一捆的紅色尼龍繩,也有黃色的,在燈照下熠熠生輝。織好的網兜子整整齊齊地紮好,堆放在客廳另一邊,也有的塞到銀霞銀鈴兩姐妹的房間裡。有一天細輝對銀霞說,你家像個盤絲洞。
他以為銀霞不懂,但《西遊記》的故事,銀霞老早從收音機里聽過了。唐三藏與孫悟空師徒等人到西天取經的路上,歷八十一劫,她能從頭數下來,一個不漏。
那時候,細輝和銀霞不過是兩個孩子。他們正好是樓上樓下兩戶人家,又恰恰是同齡人。兩家的母親還算要好,時而相互串門;往往這邊一長嗟,那邊一短嘆,便又到了做飯的時辰。巧的是銀霞的父親開德士在城裡載人,細輝的爸爸則開載貨羅厘走南闖北,同在路上謀生,勉強算運輸業同行。
細輝的父親奀仔有一回冒雨從金馬侖下山,天陰路滑,中途失控翻車,人與羅厘還有滿車的蔬菜瓜果全掉到峭壁下,摔成了稀巴爛。留下來兩孤兒一寡母,還有一個年紀比大輝只稍長几年,在他家裡長年寄居的親妹妹。銀霞從小跟着細輝那樣稱呼她,蓮珠姑姑。
大輝那時還很年輕呢,嫩得細皮白肉,瘦得隨風擺柳。他比弟弟細輝年長七歲;中三考過初級文憑試後,不等發榜便決定輟學,被父親保送到朋友的摩托店裡當學徒。他自是不肯把蓮珠叫作「姑姑」的。這姑姑也和他一樣讀不成書,十七歲即從古樓河口乘車到城裡來投靠兄長。大輝孩提時隨父母回老家過年,與蓮珠這大姐姐和其他孩子在漁村里結伴玩耍,一起捉過小螃蟹和彈塗魚,蓮珠還曾領着他登上漁船,玩過船長和海盜的遊戲。當時大輝尚且喊不出「姑姑」來,何況後來蓮珠提着兩個散發魚腥味的行李袋來到樓上樓,他已十四歲,是個生猛少年。
「大輝長這麼高了,大男孩了。」大輝放學回家,碰見母親與蓮珠坐在廳里;兩個行李袋像兩隻髒兮兮的漁村狗,怯生生地伏在她腳下。前兩年他到古樓河口過年,蓮珠與朋友出門去了,因而都沒碰上面。如今再見,她像是跳升了一個級別,忽然變成了大人,穿大人穿的收腰花裙子;用那種長輩才有的目光看他,說這種老氣的話。
「叫姑姑啦,蓮珠姑姑啊。」大輝的母親見他站在門邊呆若木雞,便開口提醒,那是姑姑,你爸爸的小妹妹。
奀仔老家有兄妹十三人,他是長男,蓮珠是老幺,兄妹年齡相差二十多歲。其時奀仔的母親未及五十,已被漁村裡的人笑她老蚌生珠。她與丈夫不識字墨,之前給一打孩子取名,兩人幾乎已殫思竭慮,於是女兒生下來便順勢叫作阿珠。大輝幼時回父親的老家,也跟着大人那樣喊,阿珠,阿珠。那時沒人糾正過他。
在古樓河口的十多年,蓮珠因為是幺女,無須上船捕魚,也不像家中的七個姐姐,需要照顧弟妹和做許多家事,因而十指纖纖,生活過得懶散,也無心向學,只想早早離開漁村,投奔城裡的花花世界。十七歲那年年底,她拿着一紙可有可無的初級文憑,帶着父母的口信到錫都來找大哥。在奀仔的指示下,他老婆何門方氏讓人用夾板在客廳一隅硬湊出一個小房間,掛上門帘,讓這小姑在樓上樓住下來。
蓮珠在舊街場一帶幾家店鋪打過工,在海味鋪稱過鹹魚蝦米,在茶室端茶洗杯,賣過洋貨;奀仔死的時候,她在休羅街上的綽約照相館打工,算穩定下來了。細輝那時才十歲,在壩羅華小念四年級,長着一雙微腫的蒙豬眼;混沌初開,連父親橫死他都不懂得悲傷。
奀仔的喪事是在新街場那頭的棺材街上辦的。組屋裡畢竟各族混雜,諸天神佛全擠在一個院子裡,沒有條件讓誰死得大張旗鼓。細輝忘了個中細節,只記得駱道院內設靈三天兩夜,他連日坐立不安,像一個紙紮公仔,又像一個花圈,在那靈堂內任人擺布。他的母親守在靈柩旁沒日沒夜地摺紙元寶,蓮珠姑姑幫忙張羅,把女賓一一帶去安慰遺孀。族中親友和父親的羅厘司機同業們來了不少,一批一批地過去圍堵大輝,對他許多的指指點點,俱言此後長子為父,要他照顧母親和弟弟,要有擔當云云。
那是細輝第一次看見哥哥唯唯諾諾——他一手撓頭,一手接過叔父輩們遞來的香煙,似乎還有點不知所措,手中的煙就被人點着了。
大輝那時才剛滿十七歲,青靚白淨,尚未學會刮鬍子,之前還一直遭父親奀仔斥罵,說他半生不熟,腦囟未生埋。細輝真記得在父親去世前,大輝不過是個尋常少年。儘管在摩托店打工了,他每周仍然有幾天要到壩羅華小後巷的書報社,與幾個穿白衫短褲的學生一起蹲在門階上,追看剛出爐的香港連環圖,又租來許多武俠小說囤在床頭,偶爾看得廢寢忘餐。禮拜天摩托店不開鋪,他總會和樓上樓的馬來仔印度仔踢足球,間或呼朋喚友組成腳踏車大隊,一起到廢礦湖垂釣,帶回來幾條巴掌大的非洲魚。父親死後他似乎不再喜歡這些了,開始抽煙,枕頭下藏的書刊,封面再不見肌肉僨張的石黑龍和王小虎,都變成了巨乳豐唇眼睛半眯的艷女,書名由《龍虎門》改成了《龍虎豹》。
群英
司機1348說,那個單眼皮高鼻樑的長腿男人,是在舊街場鹹魚街一個巷口下的車。銀霞知道那小巷有點曲折,通往壩羅華小和大伯公古廟,可那人也可能沒走入巷子。鹹魚街沒多長,但街上店鋪林立,光茶室就有好幾家,都頂着老字號賣白咖啡,人流絡繹不絕。那裡還有許多乾貨行和海味鋪,以及一家打通兩間鋪子的玩具店。那街一路往下走,還能直達二十層樓的近打組屋呢,天曉得這男人下車後最終往哪裡去。
他下車後沒有馬上離開,而是站在路旁,慢滋滋地從衣襟的口袋裡掏出香煙,點着了一根。
「我在車上有問他,是本地人嗎?他瞄我一眼,抿着嘴冷笑。」1348說。
「我嗎?我本楚狂人,來去如風,雷霆萬鈞;游過五湖四海闖過大江南北,翻過山越過嶺;勘破三界六道生死輪迴,上過天庭落過地獄了。你說我還是不是本地人?」那人眼睛眨也不眨,噼里啪啦像說了一串江湖切口。1348禁不住定睛看了看望後鏡。那人膚色黯啞,體魄精瘦,穿鱷魚牌橫紋馬球衫,脖子上戴着一粗一細兩條光燦燦的金項鍊,吊了幾個金碧輝煌的鑲玉佛牌,看起來就像是那種背上刺滿了梵文或什麼符咒的江湖人。
銀霞雖然從未見過大輝的相貌儀容,卻還記得以前在樓上樓,人們是怎麼形容大輝的。他們都說奀仔這大兒子啊,劍眉星目,長得有幾分像明星鄧光榮;跟弟弟細輝站在一起,真不像同一個阿媽生的。也因為長得相貌堂堂,那些年他才會惹出一連串韻事,讓許多女人為他撲心撲命。
「真該是吃軟飯的命呀。」銀霞的父親老這麼評價大輝,語氣里聽不出是羨是妒。
「好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銀霞無法想象。她問過細輝,你哥究竟長得有多好看?那時他們都只是小孩,瞞着大人偷偷溜到壩羅華小,在校園裡一個乾涸了無水的噴水池畔坐下來,百無聊賴地晃着腿說話。
「就是很俊很俊,像《龍虎門》裡的王小龍那麼好看。」細輝認真地想了想。
銀霞自然也沒見過漫畫裡的王小龍,她啐了一口,你這麼說了不等於白說嗎。她抬起頭來讓晌午的陽光服服帖帖地敷在她的臉上,並且用力注視眼前的黑暗。是啊,那時她還幼稚得很,因為聽蓮珠姑姑說過,世上有人僅僅用意志力就能把一隻鋼鐵做的調羹「瞪」得癱下來,她便真覺得有朝一日,自己能用強大的意志力看穿這一塊蒙着眼睛的黑布,抵達黑暗外頭的世界。
「我只知道他說話聲音不好聽,口齒不清,還成天兇巴巴的,怎麼可能討人喜歡?」銀霞確實覺得大輝很討厭,總叫她盲妹。餵盲妹,喊你怎麼不應聲?沒聽見嗎?你是盲的還是聾的呀?
還扁嘴不說話呢,變啞巴了?
好在組屋裡有個仗義的蓮珠姑姑。她總是及時出現,說大輝你怎麼欺負小孩子,你大唔透,人家銀霞眼盲心不盲呢。
蓮珠的聲音,銀霞聽着舒服。儘管只是一般的市井口吻,蓮珠說話還帶着漁村的鄉音,聽着卻像被太陽熏了一整天的海潮,灌得人耳道里暖暖的。銀霞因而以為蓮珠姑姑必然長得十分好看,連大輝那樣的人,父親死後,他對自己的母親也敢惡聲惡氣,碰着蓮珠卻總是語窒囁嚅,說不過她,便粗着嗓子嚷起來,你大我才幾歲?我們還一起玩過泥沙呢!你少來扮家長。
細輝想想,自從父親離世後,大輝以一家之主自居,還真的不管對誰說話,語氣都越來越不耐煩了。有一段日子,外頭風亂雨急,學校的老師罷課,許多反對黨人被政府抓進牢裡。組屋上上下下被一種莫名的緊張氛圍籠罩,細輝注意到大人們眉來眼去心事重重。住十樓的寶華哥在報館工作,每天下班回來總被許多人攔住,問事。寶華其實在報館做的是雜差,就管着兩台傳真機,每天騎摩托來來回回好幾趟,風雨不改地到巴士總站去等外坡通訊員的稿子。但大家不知怎麼都覺得寶華是整幢組屋裡識字最多的人,還無事不曉,簡直如同廟裡的解簽人,就只有他一個懂得所有簽文,知曉一切天機。那段時期,連樓下的印度理髮師巴布也會從店裡衝出來問他,阿兄,今天誰被警察抓了?火箭黨的人被放出來了沒有?
過了巴布那一關,寶華走到電梯口還得被人喊住。那是各家各戶的父親,都像螞蟻嗅見甜食,一窩蜂圍攏過來,直讓寶華寸步難移。銀霞的父親要是正巧回來,也必然湊這熱鬧,在電梯口那裡與其他男人一起扯破喉嚨大發偉論。在院子裡玩單腳鬼捉人的孩童們,三不五時看過來,只見那兩道並排着的電梯門無聊至極,開了關,關了開,像兩張猛打哈欠的大嘴巴。
當年組屋的男人都在關注世局時事,大輝半大不小,人雖擠進去這些小群眾里,話卻終究插不進去。這些人見過動盪社會的,誰沒經歷過當年的「五一三」事件呢?時隔將近二十年了,大家提起這個仍禁不住臉上色變,對時局愈發擔憂。大輝想問卻按捺住不問,但目光閃爍,終究被人察覺他的心虛。銀霞的父親率先喊破。「五一三」你也知道?你也懂?你懂個屁!那時人家在流血,你還沒戒奶!
那天傍晚吃飯,銀霞和妹妹銀鈴聽父親說起大輝當時怎樣的氣急敗壞,下巴越昂越高,嗆人的聲量越喊越大,差點要捋袖子了,卻反而激起公憤。場中的長輩橫眉冷眼,一人贈他一句譏諷,叫他到一旁跟小孩們玩,當大鬼頭去。逼得他面紅耳赤,好一陣說不出話來,不得不訕訕走開。
銀霞的母親對於大輝怎麼被挫敗可一點不感興趣。她等口沫橫飛的丈夫終於把話說完,才輕聲問,怎麼樣,不會亂起來吧?
「山高皇帝遠,要亂也亂不到這裡來。」老古好整以暇,「馬來人變精了,知道打蛇要打七寸。人家要捉大魚,我們這裡只有魚毛蝦仔。」
母親一般不會追問下去,再問男人會嫌煩,而且她也實在不知道還能問什麼。她擰過頭,一個勁兒催小女兒銀鈴張口吃飯,又把餸(sòng)菜夾到銀霞碗裡,再三扒兩撥,大口大口地把飯菜送進自己的嘴巴。
銀霞的母親梁金妹,近打組屋內人稱「德士嫂」,自小埠布仙鎮嫁來錫都之前,一直待在娘家幫忙製作粗葉粄和枕頭粽。每天除了搓粉和蒸糕,她還得幫忙照顧五個弟弟妹妹,家裡沒條件讓她上學,因而她一輩子識得的字沒比女兒銀霞多。那時她在小鎮大街上擺檔賣茶果,糕點賣得不錯,人卻銷不出去。眼看摽梅快過,好在這時候蹦出個城裡來的德士佬,天天光顧,最終以兩張黃清元登台的入場券成其好事,不久後即把她迎娶到錫都。
德士嫂在錫都定居逾十年。前面七年在新村,後來遷到組屋,多數時候都窩在家中,在這城裡始終人生路不熟,對於國家大事也沒多少認知和洞見,然而不懂卻不意味她漠不關心。樓上樓的婦人自有她們學習國事的管道——馬票嫂每周來寫萬字票,像是帶上點心糖果似的,必會捎來各種時事新聞。
馬票嫂活躍於新舊街場,是當年少見的以摩托代步的婦人之一,足跡遍布近打河兩岸。從河這一邊的近打購物中心和十三間,到河另一邊的市場街二奶巷鹹魚街,乃至於靠近火車站的大鐘樓和小印度,幾乎無人不曉得馬票嫂這號人物。
馬票嫂的丈夫有黑道背景,據說曾在牢獄裡七進七出,每次出來都要在身上加點什麼刺青留念。她本人倒總是和顏悅色,言行不帶一絲煞氣。組屋上下二十樓,接近三百戶人,每一家都把她當好朋友。銀霞記得自從近打組屋落成,她們舉家搬來時,馬票嫂已經像包租婆似的,經常到各樓層視察。大家都知道她的消息靈通,雖是婦道人家,政治的事卻懂得不少,這麼多年大選時那些印在競選海報上的頭像,她全叫得出名字和黨派來。而且她不嫌煩,有叩必應,走一家說一家,還比媒體人寶華哥說得更深入淺出,生動精彩。銀霞小時候十分敬畏這位能言善道的婦人。她不僅能說廣東、客家、福建和潮州等各種方言;在樓下遇理髮師巴布,能以幾句淡米爾話你來我往;說起馬來語更是行雲流水,抑揚頓挫有味,聲腔韻致十足,叫人辨不出來說話者祖籍梅縣,是個唐人。
在發現這語言能力之可敬以前,最先讓銀霞對馬票嫂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她那可畏的記憶力。那時候銀霞以為這世上大概就唯有馬票嫂能做到了——把一整本《大伯公千字圖》都記到腦里。
今早一下樓就看見狗。馬票嫂,我該買什麼字?
普通菜園狗嗎?六零一。
不是,是兩隻狗在打架。爭春呢,咬得很兇,一地血。
狗打架噢,那是一二五。若是狗咬人,買八七九……對了,後來有看見狗交尾嗎?狗交尾是一七七。
那一本《大伯公千字圖》,銀霞家裡也有一本。此書長銷,時至今日,細輝的店裡還在賣着這本粉紅色的小冊子。他每次給這書補貨,總禁不住想起以前在樓上樓,銀霞讓他幫忙,沒花多少工夫即把整本千字圖,從零零零的螃蟹到九九九的碗櫃,其中還有些不明其義的,她都一件不漏地背下來。馬票嫂說了不起呀這孩子,有一天竟然把一本狀似日曆,厚如松糕的《萬字解夢圖》夾在腋下帶了過來,讓銀霞有空的時候也背一背。
「搞不好以後你可以幹這行,當一個馬票妹。」
馬票嫂也許沒把話當真。這麼說時,她被銀霞的母親瞪了一眼,頓時忍俊不禁,賠着笑「啪」的一聲,狠狠打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那時銀霞畢竟是個孩子,還真的夢想着有一天能像馬票嫂那樣,做一個四通八達的人,到哪兒都廣受歡迎。可惜的是那一本《萬字解夢圖》厚得堪比牛津英漢字典,裡頭的中文也比之前的千字圖艱澀許多,其中好些字細輝念不出發音來,便很快失去耐性,因而在銀霞決定放棄以前,他先投降,託詞學校要考試或是老師給的作業太多太難,一溜煙似的躥到巴布理髮室找拉祖下棋去了。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複製、摘編、改寫及進行網絡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
本文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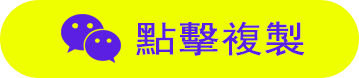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每次有疑惑都會請教,你們對我的幫助真的很大,謝謝!
求助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
如果發信息,對方就是不回復,還不刪微信怎麼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