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內容為虛構故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1
顧晟將離婚協議遞給我時,距我們那場被無數媒體爭相報道的「世紀婚禮」剛好過去兩個月。
他穿灰黑色西裝,沒系領帶,襯衣領口兩顆扣子鬆開,眼底一片烏青,凌亂、狼藉。整個人瘦得厲害,像是骨頭撐不起皮肉,五官俊逸的稜角被削得更加深邃,沉默陷在沙發上時宛如古希臘的雕塑。是憔悴的,卻也是漂亮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麼狼狽,哪怕之前他的公司深陷泥潭幾乎破產,他依舊是從容不迫雲淡風輕的。
協議書很厚,他是個妥帖的人,從生活到工作向來是面面俱到,包括離婚。他將名下幾乎所有的房產和百分之三十的股份給了我,出手很闊綽,但也是理所當然。因為他公司的起死回生全靠我和他的這段婚姻。
我翻閱的時候聞到一股雪茄味,香煙終端一點幽紅的光掠過紙張邊緣,淡藍的煙霧盤桓在他的簽字上。
顧晟之前從不抽煙。
在我翻看期間他統共抽了十根煙,水晶缸里煙頭橫七豎八地躺着。他抽得很急,煙灰來不及彈,落在地上鋪了厚厚一層。不像是品味或者放縱,是純粹的發泄。
我咳笑一聲,他終於抬眸隔着煙霧與我對視,我便又笑:「你這是卸磨殺驢呢,還是過河拆橋呢?」
他眼底兩簇恍惚的幽火仿佛在燃燒生命,玩笑話被他當做了談判桌上的交鋒:「不滿意的話,我可以再給你百分之五的股份。」
這讓我想到我朋友謝琦的話,顧晟這個階層的人信奉的行事準則便是世界上沒有錢解決不了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是錢不夠多。我當時和他據理力爭,顧晟絕不是這樣的人。
到底是我情人眼裡出西施,於是我拿筆瀟灑地簽上自己的名字:「不用了。明天上午九點半,民政局門口見。」
當晚我被失眠席捲,樓下車輛往來,從床簾中透出的微光忽明忽暗。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盯到了凌晨四點還是毫無睡意,便起來化妝。收拾完畢後我看了看腕錶,用了整整四個小時。
清晨的陽光灑在鏡面上,光中的我自己妝容精緻,從頭髮絲武裝到腳後跟。如果曾用力地愛過,那麼告別的時候也應該用力一點,隆重一點。
不過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因為顧晟又遲到了。我頂着太陽踩着高跟鞋等了半小時,終於等到他的車。灑水車剛過去不久,他猛然的剎車濺了我一身泥點。
我通過車窗玻璃看到了自己的臉,還好妝沒花。從車裡走出來的卻是陳靜,我與顧晟結婚又離婚,全都和她有關。
她很年輕,連惡意都單純,刻薄地問我:「離婚的感覺怎麼樣?」
我笑眯眯地看她:「總比連婚沒結過感覺強。」
她畢竟閱歷淺,臉又紅又白,過了一會將手放到小腹處,故作居高臨下地姿態對我笑。「那又怎麼樣?我懷孕了,至於你——顧晟碰過你嗎?」
我內心驚濤駭浪,卻維持着表面的平靜,靠近她,聲音低卻曖昧:「你怎麼知道沒有呢?」她猛地後退,杏眼圓瞪,像只即將發作的野貓,張牙舞爪撓人前,顧晟終於來了。
他擋在我和陳靜之間,眉宇間有股倦色,低頭對女孩說:「靜靜,鬧夠了就回家。」語氣不像生氣,反倒很疲憊。
陳靜又瞪了我一眼才離開。顧晟走上前推開民政局的玻璃門,朝我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我的手扶在門沿,隔着玻璃與他對視:「遲到可不是紳士的作風。」
他似乎很意外我會這樣說,愣了一下,竟輕輕笑了,自我們結婚以來第一回:「和一個小姑娘鬥嘴也不是淑女的修養。」
我們相視而笑走到登記處。人間百態在這裡輪番上演,反目成仇、痛哭流涕、亦或者形同陌路,襯得我和顧晟格外和平。
分別時我叫他的名字,他回頭有些詫異地看着我,我對他微笑:「你能吻我一下嗎?」
他沒說話,眼神看不出情緒,瞳孔上映出我的影子。我嘆了口氣退而求其次:「那抱我一下,可以嗎?」
他終於開口,卻是兩個字:「抱歉。」
我沒很失落,因為在意料之中,笑着對他說:「祝你一切都好。」
「你也是。」
走到大街上時陽光刺得我忍不住眨眼,一滴水砸在手背上。真奇怪,是下雨了嗎?
2
離開民政局後我第一個見的人是董譽。我離婚的事在網上已經傳得沸沸揚揚,因狗仔偷拍到我和顧晟站在民政局門口的照片,直接登頂熱搜第一,大有擠爆服務器的架勢。有位娛樂博主煞有介事地分析,說我在結婚前就被金主包養多年,顧晟受不了頭頂綠色才憤而離婚。
評論區被我的粉絲攻陷,叫囂着博主造謠。我覺得挺諷刺,因為我的確有金主。
我和董譽站在落地窗前,他從背後環住我的腰,靠在我耳邊輕聲道:「顧晟真沒碰過你」
他說話時熱氣在我耳邊徘徊,古龍香水混着乾燥的煙草味。我沒有回答,他便又說:「這個賭約你贏了,想要什麼嗎?跑車怎麼樣?」
我漫不經心地嗯了一聲,等到家時他的助理髮來一堆新跑車的照片讓我挑。我盯着手機屏幕,想到的卻是第一次和顧晟說話的場景。
他是位傳奇人物,出生名門,少時父母雙亡,家族企業被人算計以至破產,幾乎算是白手起家打下了自己的商業帝國。我在電影招商會上見過他幾次,第一次對話卻是在某位名流舉辦的慈善晚宴的電梯間。
我對着亮如鏡面的不鏽鋼牆補妝,顧晟在此時進來,我與他生生打了個照面。他轉身背對着我,我將口紅放回包中。
幾年在娛樂圈摸爬滾打,我早不知臉皮為何物,短暫的驚愕後便回頭對他露出一個完美的笑,嘴角的弧度都恰到好處:「偷看別人化妝可不是紳士的作風。」
他側頭看我,半張臉藏在陰影里,笑的時候俊美異常:「當着陌生人的面化妝也不是淑女的修養。」
我之前聽到過許多關於顧晟的傳說。在這個養一個情人算忠貞不渝,無縫銜接也能被稱讚一句有始有終的圈子裡,他身邊自始至終沒出現過女伴,和那些平均兩三個鶯鶯燕燕簇擁大佬們一比,簡直鶴立雞群得過分異常。
所以當我和顧晟一同出現在大廳門口時,宴會上男男女女地目光都聚了過來,好奇和探究匯成浪,對着我和顧晟兜頭澆下。
宴會快結束時謝琦端着高腳杯走到我面前,笑得意味不明:「厲害啊朱未希。」
我解釋道:「偶遇。」
後來董譽不知道怎麼聽說了這件事,他情人眾多,我和顧晟之間的捕風捉影他倒不在意,讓他感興趣的是別的方面。
「我記得顧晟有位談婚論嫁的女朋友,他這麼守身如玉,的確難得。」他攬住我的腰,另一隻手晃着紅酒杯,酒液滑過杯壁留下稀薄綺靡的紫,有幾滴濺在了手背上,我平靜地幫他吻去。他似乎很滿意,扣住我的後腦勺:「不如你去試試他能不能對你坐懷不亂。」
我當他是開玩笑,卻沒想到他真來了興致:「打個賭怎麼樣,賭他不能。我贏了就放你自由,你贏了就繼續留在我身邊。」
他脾氣古怪,向來讓人琢磨不透。我便乖巧地往他懷裡靠:「那我肯定會輸。」他順勢撫摸我的長髮,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看:「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對我多深情呢。」
說完便捏起我的下巴迫使我和他對視,他陰晴不定的脾氣我早已習慣:「你會贏的,因為你不了解男人,也不了解你自己有多漂亮。」
3
知乎上有個問題「漂亮女孩生在窮人家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某種意義上算是為我量身打造。
我家的確很窮,上大學之前我沒有一件衣服是合身的,而且都是男裝。小時候是為了穿過之後給弟弟穿,等弟弟長得比我高了,我也便只能撿他的舊衣服。
而我也的確很漂亮,父母聽說當明星賺錢便送我去藝考,面試的時候妝都沒化,才藝展示環節我做了一段廣播體操,硬生生憑着一張臉擠掉千軍萬馬過了藝考的獨木橋。
即使在美女如雲的電影學院,每當我穿着十幾塊錢的白襯衣和洗得發白的牛仔褲出現在校園主幹道時,也總能吸引一路目光追隨。
上天似乎總對漂亮的人格外優待,也格外殘忍。班主任會主動幫我介紹劇組,副導演給我安排了一個戲份還可以的小角色,攝影師免費給我拍寫真,導演以講戲為由將我帶到房間灌醉。
我流了一整天淚,打算報警時父親打來電話,他從未給我寄過生活費,但開口便是要錢,弟弟高考落榜,復讀需要高昂的擇校費。我又坐了一夜,等眼淚風乾在臉上時我給導演打了個電話。
墮落最難的莫過於邁出第一步,之後就會發現沒有什麼原則和底線是不能拋棄的,直到遇到了董譽。
董家因海運發跡清末,解放後去了美國和香港,發展到現在家族人脈遍布各國政商界。董譽是家裡的小兒子,生意方面有哥哥姐姐撐着,他只負責吃喝玩樂,線多得花不完了就搞搞投資,成了國內大半影視公司的股東。
我當時被人領到一間四面鄰水的湖中庭院,古色古香的客廳里全是年輕漂亮的姑娘。董譽坐在沙發上撫摸懷中的孟加拉幼虎,面前擺着半人高的綠植,他輕描淡寫的目光被枝葉分割成密不透風的網,不動聲色地捕捉着自己的獵物。
引薦我的人提點過一句,以董譽的身份地位他什麼環肥燕瘦沒見過,要多花點心思。於是等助理念到我的名字,我脫掉衣服跳了支剛學的芭蕾。
連眼皮都沒抬過的董譽居然抱着幼虎朝我走了過來,在巴赫的圓舞曲中伸手攬住我的腰,呼出的熱氣噴灑在我頸後。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卻仍保持着前點地的姿勢。
「別跳了,太醜了。」
我感覺自己在巴赫的注視下結成一塊冰,又被董譽的下一句吹化。
「但是你不穿衣服的樣子,還真挺好看的。」
我就這樣留住董譽身邊。他說我像張白紙,他可以親筆塗抹作畫。我原名叫朱亞男,連筆畫都透着重男輕女的名字,被他改成朱未希。他為我念江淹的賦:春陽始映,朱華未希,他說只有這個名字才配得上我的美麗。
他情人無數,對我並不算上心,但足夠耐心。從葡萄酒鑑賞到高爾夫滑雪,這些上流社會的愛好和運動都是他親自教我。有段時間他沉迷雕塑,我成了他的模特,雕好之後他送給了我,低頭輕輕吻我的眉心:「你是我最好的作品。」
因他我的影視和時尚資源也得到了飛升,成為圈內羨慕的對象。但我其實很怕他,有次他讓我品嘗法國兩個莊園葡萄酒的區別,我因胃潰瘍不願喝,他便捏住我的下頜一杯一杯灌進去。他走之後我抱着馬桶吐出了血,手機里閃爍的消息是弟弟催促我給他打生活費。我看着鏡子凌亂蒼白的自己,心想這一生這麼長,該怎麼熬過去呢。
直到我認識顧晟,直到我和董譽的這個賭約。
4
最開始我利用董譽的人脈參與了一場顧晟出席的飯局。我穿着低胸小黑裙坐在他旁邊,幾杯酒過後裸露的皮膚上燒起奢靡的艷色,他目不斜視,問我需不需要把空調溫度調高一些。
飯局結束後我裝醉往他身上靠,他用手掌抵在我肩頭輕輕將我扶正,而後交給司機。我坐在車上伸手捉住他外套衣角,也拉皺了他的眉間。我貪戀羊毛絨的柔軟和溫暖,忍不住摩挲,仰頭對他笑:「顧先生可是個真紳士。」
他慢條斯理地將衣角往外抽,動作優雅,也回了一個笑。他身後滿街霓虹,所有的光都奔他而來:「希望朱小姐也做個真淑女。」
再次見面是半月後,風投圈一位聲名鵲起的新秀在私人莊園宴請商界名流,點名要我和其他幾個女明星作陪。酒過三巡,總有不安分的手腳往我身上摸,剛開始大概顧及董譽,但他和東道主相談甚歡,一個眼神都沒捨得給我,揩油便變得愈發肆無忌憚。
我向來是笑臉相迎、來者不拒,拿起香檳一飲而盡,放下酒杯時卻對上一雙不動聲色的眼睛。
顧晟端着高腳杯,西裝外套搭在臂彎處,襯衣領口敞開上面兩顆扣子略顯隨意,側頭與友人說笑,朝我送來漫不經心的一瞥。
我早就不知道廉恥二字怎麼寫了,可與他對視的那一刻,我竟不由自主地拂開一雙肥膩的手:「楊總,請自重。」
這反而招致對方更放肆的舉動,我被逼到泳池邊緣,裙子濕漉漉地貼在身上,吸引了更多不懷好意的目光。暌違多年的屈辱感撲面而來,我一咬牙轉身跳進水裡。
我現在仍記得那天的每一個細節,水花四濺的巨大聲響,我發顫的雙肩和手指,以及董譽玩味又嘲諷的微笑中顧晟遞來的那雙手。
是我在冰冷泳池中感受到的唯一暖意。
我低着頭狼狽地向他道謝,他將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小心着涼。」我不敢看他,幾欲落淚。
後來我思考自己到底為何愛上顧晟,根源總能追溯到這一刻。
我遇到這麼多人,從導演到董譽再到楊總,他們只關心我能脫幾件衣服,只有顧晟,只有他願意為我披一件衣服。
5
因為這件外套,我給顧晟打了兩個電話。第一次是問要不要清洗後給他送回去,他說不用這麼麻煩,扔了也行。於是掛了電話我轉頭便將外套送進乾洗店,去取那天給他打了第二個電話:「衣服洗好了,我給你送過去吧。」
電話那頭他沒立刻回應,大概已經忘了這件事,聲音溫和而隨意:「不用麻煩了,我讓司機去你那拿。」
我說這怎麼行呢,我好歹要當面道個謝,他遲疑片刻,說了一個地址。我沒找到紙,便將地址記在手腕上,背熟後才去洗掉,字跡如螞蟻般散開,像是爬進了我心底。
我按圖索驥開車到一棟老舊的西式別墅,庭院中幾株古老高大的梧桐樹枝葉繁茂,隔絕了市中心的喧囂,在鬧市中開闢一席幽靜。
開門的是位精練的中年女人,客客氣氣地將我請進客廳,稱我為朱小姐:「先生一會就回來了,您稍等片刻。」
她給我端來杯紅茶,我伸手去接時樓上傳來一聲突如其來的笑,而後一道纖弱的身影從樓梯口斜出。十七八歲的年紀,小巧甜美的臉上嵌着雙幽深的眼,看向我時閃過乖戾的光。
這便是我和陳靜的初見。
她家與顧家是世交,陳靜有個和顧晟青梅竹馬還訂了婚的姐姐。可惜家門不幸,一場車禍後偌大的陳家只剩十二歲陳靜,而後顧晟將她接到身邊親自照料。家破人亡讓她變得她變得孤僻而倔強,她叫顧晟姐夫,給他打下自己的烙印,將出現在顧晟身邊的女人一概視作敵人、橫眉冷對,仿佛一個時刻高度警戒的人形雷達。
顧晟到家後挽留我吃飯,我本就別有用心,自然不會推脫。餐桌上陳靜共叫了五聲姐夫,三次提及自己的姐姐,稱讚她的高貴與才華,用弦外之意將我踩進塵埃,暗諷我是個敗絮其中的花瓶。
我笑意盈盈,手指按在刀叉上將牛排切成規整的小塊送入口中,優雅得像是在彈鋼琴。董譽曾握住我的手親自教我,他說女人的纖纖十指執刀時為有種割裂的美感,他喜歡看。
慢條斯理地將牛肉咽下去後,我才回她:「那陳小姐應該向令姐多學習一下。」
她果然不經激,揮手便扔下刀叉,清脆的碰撞聲中竹青色瓷盤裂開一塊豁口,碎瓷片迸出砸在顧晟的手背上。他放下餐具,在陳靜說出更惡毒話之前開口制止:「靜靜,聽話。」
晚上有個綜藝的通告,顧晟開車送我去拍攝地的路上向我道歉:「靜靜她年紀小,你別和她一般見識。」
她是真的年紀小,所以天真,所以直率,惡意都不帶拐彎抹角,對我這樣的人卻毫無殺傷力。哪怕她是害我和顧晟離婚的罪魁禍首,我也從未覺得她有什麼可怕。
這段關係中我真正怕的人是鄭莎——顧晟的正牌女友。
顧晟的車與許多車都不同,特殊在氣味上,瀰漫着白檀和某種草本植物的清香,吸入時仿佛能洗滌靈魂。不像其他的車,各式各樣的香水味混着萬年不變的煙草和汽油,我整日乘坐,將自己也醃成同樣繁複的味道。
於是我問他:「你不抽煙嗎?」
從車內後視鏡里我看到了他的笑,令我想到初春的風,所到之處冰消雪融,是我之前從未見過湛湛溫柔:「年輕的時候抽,我女朋友讓我戒的,她是田徑運動員,最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車輛剛好從高架橋下穿過,橫樑巨大的影無聲砸下,疼得我鼻眼發酸。
這是我與鄭莎的第一次交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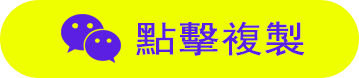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文章我看過,感覺說的挺對的,有問題的話可以多去看看
可以幫助複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