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娜在遺書中寫道:「希望以後大家能多多關注抑鬱症這個群體吧,願這個世界多些善意和美好,少些傷害。」
文|新京報記者衛瀟雨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范錦春
馬鳳丟下筷子,給林娜打電話,沒人接,再打,依舊沒人接。林娜大學時期的輔導員給她打電話:「快,馬上聯繫峨眉山景區派出所!」

下午兩點,林娜的高中同學高琪,看見宿舍QQ群有人問,能聯繫到林娜嗎?舍友們找到當地派出所報了警。六年前,林娜自殺過一次,被救回來一命。這次,她們寄希望還能救回來。
下午四點多,馬鳳接到電話:林娜走了。
馬鳳在新聞里看到女兒離開時遊客拍下的視頻。視頻僅有一分多鐘,林娜站在「捨身崖」邊緣,這個山崖在近一月內已有三人跳崖。林娜兩次雙手合十、舉過眉心,遊客聚在圍欄外勸她,她一言不發,向後退了一步。最後,林娜張開雙臂、兩腿一屈、向後倒下,像一隻失重的鳥。
高琪也點開了那個視頻,看了幾秒鐘就確認了,是她。她關了視頻,連續幾天不敢打開微博熱門,擔心再刷到那個視頻。宿舍群里確認了林娜去世的消息後,有人接了句家鄉話,「這個傻子怎麼會做這樣的事?」
一
女兒離開後,馬鳳委託親戚去了峨眉山處理後事,她待在家一連哭了四天。她沒敢告訴今年高三在讀的兒子,為了不讓兒子察覺到異常,這個家裡至今保留着林娜的痕跡,桌子上放着她買了還沒拆封的書、牙刷筒里有兩支牙刷、拖鞋擺在樓梯上原來的位置。
房子最深處,擺着去世林娜父親的遺照,四年前,林娜高考前一個月,他因為肝癌離開了這個家。林娜遺書里寫道:爸,我找你來了!
9月8日,馬鳳哭累了、哭夠了,她刪了林娜的微信,不想再去回憶。次日,她出門買菜,打算體面地做一頓飯,生活照常繼續。我見到馬鳳的時候,她穿着長裙和高跟鞋、畫了眉毛、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打開房門,客廳收拾得乾淨整潔,花崗岩地板能印出人影。
吃飯的時候,我們聊到了各地飲食差異、絲瓜的做法和辣椒,小心翼翼,沒人觸碰那個沉重的話題,最後,是馬鳳主動提起來了,她26歲才生下女兒林娜,「如果像人家20歲結婚生孩子的話,她(林娜)年齡就差不多30歲了。」
去年12月林娜確診抑鬱症以後,告訴馬鳳,她整晚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得有隻手在抓她,「好痛好痛」。
馬鳳問過女兒,要不要帶去隔壁的大城市治病?林娜說,她要自己慢慢調理,並認為開藥沒什麼用。馬鳳不知道抑鬱症是什麼樣的,林娜說要自我調節,馬鳳想着「自己心裡想開了,不往那方面想就可以了」,最後,治病的事也就沒再提了。
2018年早些時候,林娜有過一次自殺表示,她在微信上給馬鳳發消息,說自己「好難過,得了這種病(抑鬱症)」,問她,「如果我死了,你會怪我嗎?」
馬鳳沒法理解她的痛苦,「我又沒得過這種病,我哪裡知道有那麼痛苦?」女兒的病,超出了她過去四十多年的生活經驗,她回復女兒:「如果你死了的話,我也跟着你去死」。
馬鳳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轉而求助迷信,花一百塊錢找了位神婆。神婆說,是有小鬼纏住林娜了,她已經給下面傳了話。神婆遞給馬鳳一碗清水,往裡面摻了燒紙的灰,讓她倒掉,說這就是給林娜改了命,她馬上就能痊癒。
馬鳳從林娜的表現來看,神婆說的話奏效了。春節,林娜回了家,馬鳳覺得她看起來就像正常人一樣,她找了份教小孩子的工作,上了班、忙起來,好像已經忘記痛苦了。她帶着弟弟去桂林玩,和弟弟一起打籃球,回高中學校跑步,還考了駕照。
馬鳳每天叫女兒一起出去散步,給她做好三頓飯,需要錢的時候拿出來給她,林娜辭職換工作支持、不工作出去旅遊也支持。
林娜想當兵,為了達到體重標準,她在家減掉了七八斤體重。8月,林娜去昆明做徵兵體檢,希望能進入部隊,一切看起來都即將走上正軌。
8月31日晚上十一點半,馬鳳準備睡覺的時候接到了林娜的電話,告訴她,「我這次(徵兵體檢)又沒過」。這是林娜第二次徵兵體檢沒通過,上一次是2016年8月。
林娜確診抑鬱症後,馬鳳曾經問過女兒,「你預計是什麼時候開始了?」林娜沒接話。「是不是沒去當兵對你打擊蠻大?」林娜說:「也許吧。」
這一次,馬鳳安慰她,「沒過就沒過,也還能找別的工作,不一定要當兵」,林娜應承着,答應「過兩天我就回來,你去睡覺吧」。
幾天後,馬鳳從林娜的朋友圈看到,她從昆明跑到了四川,在峨眉山蹦極,她看起來很開心。9月4日,林娜發在朋友圈的照片,是兩座平行的山峰,雲霧繚繞,配的文字是「這裡很美」。馬鳳看了,沒發現絲毫異常的跡象,她還等着女兒「過兩天就回來」。
二
林娜跳崖自殺前,已經釋放出危險信號。在馬鳳看不到的qq空間裡,林娜在跳崖的前一天感慨「能得道嗎?」晚上,她還轉發了知乎上的一篇回答,「一個人到底絕望到什麼程度能讓他想要去死?」
那篇回答寫道:「所有困境都是來自,一切都不會改變。『自殺之人都是最想好好活下去的』,太想好了,破解不了面前死局,又無法坦然接受絕望,便只好一走了之。」
兩個人剛認識的時候,林娜經常自殘,在手、胳膊、大腿上用刀劃很深的口子,身體上幾乎沒有乾淨的地方。高琪見過林娜一個人呆着的樣子:坐着發呆、一動不動、眼神空洞,她會盯着自己的傷口看,把結痂的傷疤摳開,傷口反覆流血。她把傷口的照片發在QQ空間,形容成「為了尋找一種疼痛的存在感」。
高琪猜測,在那時,林娜可能已經患了抑鬱症,她頻繁提到死,和父母關係不好的時候,她說「如果不是有奶奶,我就已經去死了」,和朋友吵架,她說「沒有人關心我,我就去死了」。
有數據顯示,抑鬱症終生發病率高達10%-15%,是所有疾病中自殺率最高的一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抑鬱症患者達3.5億人,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可能成為僅次於心腦血管病的人類第二大疾病。
但高琪不了解抑鬱症,林娜也沒有去正規專科醫院進行抑鬱症的診斷。北京市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副主任醫師趙茜說,現在無法判斷高中時的林娜有沒有達到抑鬱症的診斷標準,但當時,她至少表現出了青少年抑鬱的特點。「如果有自殘、自傷等表現,或者達到了中度以上的抑鬱症,影響了學習、生活,一定要接受系統治療。抑鬱症作為反覆發作性疾病,一旦確定診斷,只有接受正規醫院的規範系統治療才有臨床治癒的可能,自我調整或許可以短暫緩解,但根本達不到治療的目的。」
高琪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她,確實在用一些偏激的行為對抗抑鬱」。高二時,林娜因為感情波折試圖自殺過一次,朋友趕到家裡時,她已經吃了五十多片安眠藥。被帶去醫院洗胃,才救過來了。
在高琪眼中,林娜敏感,「她不會很直接地去表露自己的情緒,她覺得自己那麼敏感、能夠感覺到別人,她需要一個能夠給她無條件的關心和愛,能夠很理解她的人。」
林娜期待生日,會想很多辦法教高琪記住自己的生日。林娜把生日的數字拆解成好記的短語,每到了生日臨近的一個月便時不時暗示,有人快要生日啦!或者是主動提到,等高琪生日,她要送禮物、帶她去玩。
「她會非常反覆地強調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學業和生活之前」,高中,兩個人在操場散步,有男生踢球,一隻球朝着她們飛過來。高琪下意識地攬住林娜,她忽然轉過身來,一本正經地告訴說:「以後不管你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幫你。」
高中,林娜是學校里少有的走讀生,每天下了晚自習已經快到夜裡十點。有幾次到家以後,林娜發現,媽媽已經鎖上了門。她性格敏感,又有股子倔勁兒,隔着一道門,林娜不願意主動敲門、馬鳳也沒主動打開,最後,林娜騎車返回學校,在操場旁邊一個儲物間裡睡了一晚,沒有空調、沒有被子。
高琪去過林娜家裡兩次,甚至「不敢和她媽媽打招呼」,每次是夜裡悄悄過去、早上凌晨五點多鐘悄悄走,她和馬鳳在客廳里撞上過一次,誰也沒主動說話。但馬鳳不記得這些了,她說她不認識女兒的朋友。
三
馬鳳喜歡打聽從林娜高中同學那裡聽來的消息,透過這些才能知道女兒對自己的看法。她逐條否認了女兒曾經對自己的「指控」,林娜總覺得母親偏心弟弟,家鄉小城有生兒子的傳統,當年為了生弟弟,馬鳳大着肚子在外面躲了五個月、交了一萬塊錢的罰款。馬鳳卻說,她對女兒比對兒子更好。
馬鳳回憶起林娜的自殘,說,「你說那些傷啊?」語氣聽起來有些輕描淡寫,她把那歸為初中時期的叛逆。小學的時候,林娜留着長頭髮,是爸爸媽媽的乖乖女,到初中,她自作主張把頭髮剪短到耳朵的長度,高中,剪成了男孩一樣的寸頭。隨着頭髮越剪越短,馬鳳越來越管不住她,「她自己有想法了,她不聽你的。」
管不住的同時,她又沒有徹底鬆開女兒,「你本來就是一個女孩子,你幹嗎去扮成男孩子那個樣子?」這讓林娜倍感壓力。
為林娜收拾遺物的時候,馬鳳發現了一封信,夾着一張女孩的照片。信里,女孩叫林娜「老公」,林娜叫她「媳婦」,透露了兩個人租房子同居。馬鳳曾經在兒子手機上看到林娜QQ空間裡有兩個女孩的合照,臉貼着臉。
「她其實把我女兒當男人了。」馬鳳不理解同性戀的概念。
母女倆的溝通很少,林娜說倆人有代溝,又嫌棄馬鳳沒讀過什麼書,聊不到一起去。馬鳳工作忙,她近幾年才學會用微信,到現在都不會用QQ。她用兒子的QQ看過林娜的QQ空間,知道她寫詩、寫文章,但她看不懂。
馬鳳給女兒的陪伴太少了。對馬鳳來說,陪伴孩子、賺錢養家是兩個矛盾的選項,過去,她和丈夫全力在賺錢、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最終給家裡蓋了四層樓的房子、兩個孩子都就讀於當地最好的高中,順利支持林娜讀完了大學,已經算是對孩子足夠用心的家庭。丈夫去世後,馬鳳一個人打工支撐着兩個孩子的生活,一周七天連軸轉,晚上九點半才能下班。
馬鳳至今記得,丈夫剛去世的時候,她和女兒林娜談心,告訴她,「你是這樣的家庭,你自己要聽話。」林娜的回答她放心,「等弟弟之後上大學了,我會資助他的,那時候我就大學畢業自己有工作了。」
高考後,馬鳳提出讓林娜復讀一年,她沒同意,自己報志願、選專業,挑了個要坐兩天兩夜火車的城市,然後自己拿着行李開學報到、辦理助學貸款。朋友圈成了馬鳳了解女兒的主要渠道,她去了麗江、買帳篷,一個人去露營、想去部隊當兵,馬鳳都是看了朋友圈才知道。
我在馬鳳家待了一個下午,陪着她做飯、去藥店擦藥,她膝蓋有毛病,腰也不好。她說林娜從來沒有和她聊過這麼長時間。「跟她就是十分鐘都不給你,你說到她不開心,她發脾氣扭扭頭就走。」
有鄰居來家裡看望馬鳳,林娜的照片就放在一旁的椅子上,鄰居拿起來照片,一張一張翻着,每一張林娜都笑得開心。
馬鳳帶着哭腔,用家鄉話說,「全國人民都曉得我女兒死了!」
四
無法從家庭里獲得的關愛,林娜曾經從朋友那裡獲得。高中時期,高琪每天帶着晚飯去陪林娜。
林娜不願意回家的時候,就去學校操場的儲物間住。當時在住校的高琪把自己的朋友介紹給她,她是那種「只要一有人能夠給她關懷,她就能夠好像是忘掉自己心裡的一些東西,努力去給別人帶來快樂的人。」
在朋友的陪伴下,有段時間,林娜看起來在好轉了,她自殘的情況變少,從自己的情緒里走了出來。周末下午,朋友們經常一起去學校操場曬太陽,在草地上躺成一排聊天。她們聊明星、聊八卦、聊喜歡的老師和考試卷子題目很難,聊一切無關緊要瑣碎的事。對這些話題,林娜不感興趣,但她會努力參與進來,跟着一起笑。
林娜的選擇並不是個例。《2017年中國網民抑鬱症調研報告》顯示,當個人可能出現抑鬱情緒時,只有5%的人表示會尋求專業機構或個人的幫助,而其他95%則選擇忍或者跟親友傾訴。抑鬱症患者得到系統治療的只占總人數的10%左右。
半年多以後,林娜對高琪的依賴甚至到了讓她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沒有及時回復林娜的消息,她會變得敏感,反問「你是不是同時在跟很多人聊天?」她必須一邊洗衣服、做飯,一邊回復林娜的每一條消息。到後來,如果兩分鐘內沒有回覆,林娜會覺得受不了,反反覆覆地問,「你是不是覺得我很討厭?」
高琪告訴她,你要有自己的生活,要處理好自己的狀態,你不能依賴我。同時,她開始疏遠林娜,林娜約她吃飯,她就找理由說沒時間,她不接電話、不回消息,慢慢地,林娜不再找她了。
高中畢業後,兩個人幾乎沒聯繫過,高琪也只能通過QQ空間知道林娜的動態。QQ空間裡,林娜展示自己和朋友們一起玩,一切看起來都在變好。高琪甚至一度把林娜當做正面的例子講給身邊的人:她對自己有明確的認知,儘管時常因為外形和性取向受到壓力,她從沒想過改變自己,並且,她積極治療、主動和人溝通、她不抗拒袒露內心。
林娜離開以後,高琪重新回顧,才意識到可能她過得並沒看上去那麼好,「她給我的感覺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表現得很開心,讓大家都不要擔心,但實際上從很細微的包括語氣中能感覺出來,她也並沒有那麼開心。」QQ空間裡,林娜每條動態評論的人很少,「應該說並沒有那麼多人去配合她做那種表達。」
在醫生趙茜看來,有一類抑鬱症屬於微笑型抑鬱,這類患者往往在別人面前不會表現出內心的真實一面,內心的壓抑、痛苦、憂愁反而會比表現出抑鬱的患者更嚴重,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和平時正常的狀態差不多,但實際上和內心的狀態是不一致的,壓抑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
林娜留下的遺書,高琪反覆讀過很多遍,她記得裡面提到的每一個細節。林娜寫,她換了工作,高琪想起來,她甚至不知道林娜工作過的事。
高琪開始反思,當初沒有處理好兩個人的關係,她突然的疏遠可能給林娜帶來了壓力。「也許我們原本是有機會讓她真真正正地痊癒。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對抑鬱症沒有那麼明確的概念。」
五
看到林娜跳崖的新聞,高琪才意識到,林娜實際上是病得更重了,「以前她還能夠外露出來,願意讓別人知曉,到後來她好像已經完全封閉了,就只是裝作很正常的樣子。」
病得嚴重的時候,林娜整晚睡不着,「就像一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一點、一點的把我的靈魂從身體裡拖出來,然後一天、一天地把它拖進深淵裡。」在家裡,她拿着手機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一整天,只有吃飯和上廁所會下樓。高中時期的朋友們都在外地讀書、工作,沒有人能陪她說上幾句話,街坊鄰居全都是老人。
林娜常常會在高中的宿舍群挑起話題,提到又回了高中的某處、遇見了共同的熟人,感慨,「一中變化還挺大的」,她問「你們現在在家嗎」,組織「大家一起聚一聚」。林娜上一次在宿舍群里說話是在6月,凌晨十二點二十,「好久沒見面了」。讀大學後的四年,舍友們都在外地,她們也只聚過一次。
「她是不斷地希望去回望過去,待在一起曬太陽的日子,但好像大家都已經各自往前走了。」高琪說。
馬鳳一直在尋找女兒自殺的原因,「她得了這個病朋友都知道,有沒有一個人真正地關心?對她關心了解,她都不會這樣子。」她認為女兒的抑鬱症是自己工作太忙陪不了她,又沒有知心朋友可以傾訴,才一步步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
有數據顯示,中國有八千萬抑鬱症群體。浙江大學醫學院神經生物學教授包愛民表示,我國的年自殺率達到30萬人,這個數字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三倍,這是抑鬱症病人沒有得到很好的診治造成的。
許多抑鬱症患者都被忽視了。林娜跳崖時,同在峨眉山的遊客高偉身邊也有抑鬱症患者,他形容:「大多又不願讓家人擔心和誤解,所以他們在人前還要表現得像個正常人」。抑鬱症患者秦寬看了林娜的遺書後,「感覺每一句寫的都是自己」。
林娜跳崖的後一天,抑鬱症患者趙璐看到林娜在遺書里寫道,要想辦法自救。「媽,我可能有抑鬱症」,趙璐試探性地告訴母親,她小心翼翼地用了「可能」,媽媽沒聽清,回了句「什麼?」
隔了一會,趙璐重新鼓起勇氣,「我有中度抑鬱症」,媽媽轉過身,走到餐桌旁拿走手機,說了句,「我看你有神經病」。最後,叮囑她吃完了把碗洗乾淨、衣服洗了。趙璐回頭看了媽媽一眼,她頭也沒回便去了旁邊的房間,「我想我裝成正常人的樣子真的成功了……我想我也快要解脫了!」趙璐說。
現在,在已經去世的林娜家裡,依然到處都是「福」字,對美好生活的祈願填滿了這間屋子。這樣喜慶而吉祥的氛圍,顯得不相稱了。這棟四層樓的大房子裡,如今只剩下馬鳳一個人,她斜靠在搖椅靠背上,一隻手擋着眼睛,「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就是這樣子。反正她都不要我了,她丟下我,我也沒有辦法。」(來源:新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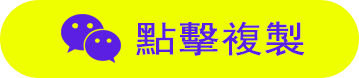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情感分析的比較透徹,男女朋友們可以多學習學習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