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時客戶端-錢江晚報記者 張瑾華 通訊員 馬正心
2 年前的一天,作家蘇滄桑打點行裝,深入老家台州一個草根戲班,與「做戲人」同吃同住同演戲,寫就了三萬字的長篇非虛構散文作品《跟着戲班去流浪》,2018元月發表在第1期《十月》上。
2年後的今天,《跟着戲班去流浪》榮獲《十月》雜誌主辦的第三屆琦君散文獎。她說,她要特別感謝帶着她流浪的臨海吉祥越劇團沉香般美好的姐妹們,這份榮譽同樣屬於她們。這個作品,也是蘇滄桑在《人民文學》2017年第5期頭條發表的非虛構《紙上》的姐妹篇。
那期《十月》的《卷首語》中寫道:作家蘇滄桑文章真實地記錄了特定人群的生存狀態及思想情感,其真切、細微的描述,遠非躲在書齋中所能完成。我們身邊被忽略的現實人生,在文中掙脫了概念化的存在,變得如此鮮活且意味深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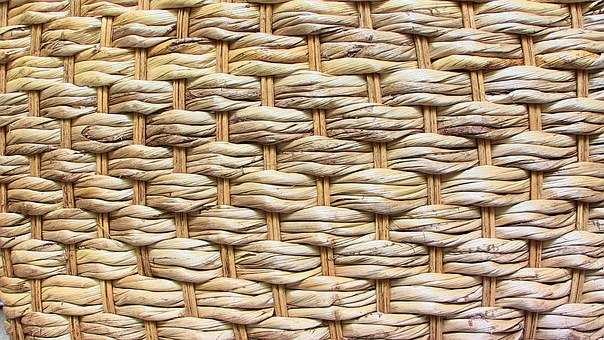
這兩年,蘇滄桑走向民間的腳步並未停下來,似乎正興致勃勃地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不能回頭了。她說,「接下來,我還想去做湖筆,養蠶,放蜂等等,書寫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美,勞動之美,人民之美。」
深入越劇草根戲班一個月,深度體驗原生態民間戲班生活。她的《跟着戲班去流浪》分「路遇、戲痴、嘟嘟、住處、小生、吃飯、扮上、唱起、拆台、過台、封箱、官人、重聚、曾經、沉香」,共15個小節,3萬字,講述大時代小戲班底層人的故事。
她回憶,自己是在人生途中遭遇了一些災禍後出發的。「出發兩個月前,我遭遇飛來橫禍,頭破血流,緊接着因聞所未聞的十二指腸憩室炎住院,五天五夜水米未進,雖僥倖未動刀,卻也折騰得死去活來。身體虛弱的人,想法便少了,原本在意的一些事一些人便淡了,沉睡在心裡很久的夢,便醒了,逸出來了。」那些逸出來的東西,「跟着戲班去流浪」,就是其中一個。
「連續四天大雨,把天都下漏了。我的身體也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狀況,一陣冷一陣熱,頭頂已經癒合的傷口隱隱作痛,隔幾分鐘,整個頭部從耳朵開始突然發熱蔓延全身,心跳加速,氣喘不上來,渾身無力。我母親勸阻,說你病剛好,元氣還沒補上,太虛弱了,腿上又被蚊子叮了那麼多毒包,天這麼悶熱,雨這麼大,戲班裡那麼苦,不要去了,等身體養好了,秋天再跟她們去吧。但我還是去了。」
為什麼偏偏要選擇「戲班子」呢一頭扎進去呢?
那是2017年芒種後的第一場黃梅雨里,蘇滄桑和父親吃過晚飯,她上三樓收拾「流浪」的行李。她記得三樓面山朝南的臥室,曾經睡過四個人——四個做戲人。三十多年前的冬天,村里請來戲班做戲,小旦小生等四個主要演員被分到她家裡。小旦微胖,面目模糊,聲音甜美,小生以極其俊美的扮相和極富魅力的唱功做功,一夜間轟動了山後浦村。她每天心跳最快的時候,是看到扮上戲妝後的她——她扮演的所有角色都像我夢中的白馬王子。
蘇滄桑深情寫到了這一段自己從小與越劇的緣份——
「我是戲痴,我的祖輩更是。月圓之夜,小漁商販出身的祖父常雇一條船,在楚門鎮南門河等青燈古、賴烏丁等一幫「狐朋狗友」一一上船。鑼鼓笙簫三弦京胡一應俱全,卻沒有女人。祖父拉京胡,他們自彈自唱,開懷暢飲。夜半盡興後,祖父哼着小調走在清冷的石板路上,一手煙斗,一手提着一碗熱氣騰騰的餛飩帶給祖母吃,他知道她會一直等他。
祖父浪漫的基因,流淌在二伯和父親的血液里,也流進我的血液里。兒時的二伯演過《野豬林》裡的林沖,兒時的父親演過《血淚仇》裡的偽保長,沒有戲服,用窗簾布當披肩,借廟裡神祗塑像的龍袍當戲服。兒時的我將越劇《紅樓夢》看了七八遍,並無師自通學會了幾乎所有越劇經典唱段。兒時的木雕床底下,珍藏着我自己縫的一個小姐布偶,鞋盒子做成她的閨房,中間用錦旗的黃色流蘇隔斷,用黑線做的雲鬢,從母親的珠釵上偷拆了兩顆珍珠做的步搖。在我眼裡,她是林黛玉,是祝英台,是《碧玉簪》裡的李秀英,是《柳毅傳書》裡的三公主,是寡言的我……她是有生命的,她與孤獨的我自成一個宇宙。
「十三歲那年,從小鎮搬到山後浦村新家時,她丟了。我想,在某個幽暗的角落裡,她已經成仙,她不願離開那間快要坍塌的老屋,她的道場。我想,有一天,她會以另一種形態回到我身邊。」
她回憶,小時候曾經有個瘋狂的念頭,就是跟着戲班子走。沒想到這兒時的夢想,如今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這個蘇滄桑老家玉環的戲班的名字叫「吉祥」。她身體跨出去後,她跟戲班子同吃同住同演戲,體驗到了封箱時的悲歡,覺得戲班子裡的他們太不容易了,也太可敬了。
農曆五月二十一,是吉祥戲班封箱日。
「我原想說,做戲多自由浪漫多開心,可短短几天,我便明了戲班生活的本質絕非原先想象的那麼美好,而是極度的勞心勞力,甚至厭倦,儘管,曾經,她們和我一樣嚮往。」她感嘆,「越深入,越深切體會到我夢想中所謂的「流浪」照進她們的原生態時,「居無定所,不斷遷移」是真,「放浪,放縱,無拘束」是假,宋無名氏《異聞總錄》中那一句「流浪千劫,不自解脫」才是她們的真實寫照。」
看到她的《跟着戲班去流浪》後,一個戲劇工作志願者對她說讀了三四遍,每讀一次都流淚。
像吉祥越劇團這樣的民團,在台州有近百家,多數民團,每年演出場次在300場以上,台州已漸漸成為全國最大的越劇市場。越劇起源於嵊縣,繁榮於上海,而在台州,人們驚喜地看到了中國越劇傳承發展的希望。戲班人員一專多能,吃苦耐勞,既唱頭肩,也跑龍套,還會「落地唱書」,深受百姓歡迎,雖在夾縫中求生存,卻自有一份榮耀、一份尊嚴。
蘇滄桑在一個月的戲班生活中,也圓了兒時「做戲夢」,扮了回小生,她老父親給她錄下了化妝、演戲扮小生到忽然笑場的每一個片段。最重要的事,她覺得自己能為辛苦求生的民間戲班做點事,紀錄下一點什麼,再怎麼辛苦也值了。
她說,「每一次深入生活,於我都是一次靈魂的洗禮。像發現篝火的傻孩子,我大聲嚷嚷,恨不得讓所有人都來取暖。」
那麼,有什麼更深遠的意義嗎?她說:「多年以後我不在了,一代代人不在了,無數記錄者的文字還在,未來的人讀到時,依然能從中觸摸到一雙雙人民的手,聽到更接近天空或大地的聲音,看到始終縈繞在人類文明之河上古老而豐盈的元氣。」
「守赤子之心,接人間地氣,信萬物有靈」是蘇滄桑的寫作觀。她在思考,漫漫人生,人的內心必然會經歷無數次價值觀的顛覆重建,文學觀的顛覆重建。她發現,越是年長,越深感自己的無知,越渴望觸摸探究世間萬物。「萬物有靈,當你念念不忘,你找不到它時,它會來找你。」這是字里字外,蘇滄桑的信念。
這也是蘇滄桑的夢。隱約,還覺得有不足,於是,又有了新的夢。
「我想與她們相約秋季,或者下一個秋季,或者某一個秋季,帶上早已備好的禮物——一個納米護膚噴霧器,繼續跟着戲班去流浪。那時,我的想法會更少,對一些人一些事會更淡,我會更像「一家人」里真正的一員,幫燒飯奶奶燒火洗碗,幫潘香背唱詞扶她上洗手間,幫賽菊她們疊戲服,幫俏俏看孩子教嘟嘟學說話寫字,跟她們好好學一段戲……」
也許,她還會繼續她的跟着戲班去流浪之路。
讀一點
嘟嘟
夜,七點半,關帝廟戲台側幕。
嘟嘟張着粉紅色的小嘴,睜着溜圓的雙眼,緊盯着正在戲台上翻跟斗的小花臉,咿咿呀呀笑着叫着,手舞足蹈。六個月大的他圓頭圓臉,氣質很像混血兒,穿一身紅色棉布衣,肩上繡着花朵和小鳥,很好看,很乾淨。隨着鑼鼓聲,他的雙腿在他的母親、25歲的小生俏俏的大腿上一蹬一蹬,一滴口水正從嘴角掛下來,映着戲台紅色的燈光。
俏俏佯裝很痛,哎呀哎呀的叫聲被鑼鼓聲掩蓋,光潔異常的臉龐在燈光的映照下,燦若朝陽。
這個戲班最年輕的演員,臨海杜橋人,面如銀盤,眉眼英武,原先主工小生,剛生了嘟嘟,暫時歇演,但戲班到哪裡,她抱着嘟嘟跟到哪裡,一滿月就出來了,整整五個多月了。
俏俏說,嘟嘟一上戲台就會特別興奮,半夜都不肯睡,做夢都咯咯笑。我也喜歡呆在戲班裡,氛圍好,開心,像一家人一樣。
這句話,讓我想起潘香之前說的「一家人」。
俏俏似乎不太愛笑。直覺告訴我她有心事,她自然不會說,我便不問。我想過,此番體驗,不打擾,不刺探,一切順其自然。對於她們,我只是一場路過的風。
每個做戲人上台前、下台後都會來摸摸嘟嘟的臉,他就無聲地笑,也許笑出了聲,但被音樂淹沒了。俏俏起身替人播放電腦背景和唱詞時,幾個做戲人便誰有空誰抱嘟嘟,誰抱他,他都笑,將圓圓胖胖的臉和兩個酒窩衝着你。我摸摸他的臉,他也笑,我伸出手抱他,他也肯。他姓金,和我一樣也屬猴。
一個嬰兒,日夜呆在廟堂里,一點都不忌諱,如同一個已過不惑之年的女作家突然跟着戲班去流浪,都是奇怪的事。一百年前,唐詩之路上誕生了唱腔委婉、兒女情長的越劇,當徽班進軍紫禁城後,南方大地上也有一群鄉下人放下了鋤頭,開始了流浪,也開始了一個百年美夢。我沒想到,第一次走進戲班走上後台,第一個遇到的,竟是跟着戲班流浪、做夢的嘟嘟。
俏俏的師傅,也就是老闆娘兼小生阿朱,穿過鑼鼓聲前來接應我。她四十歲左右的樣子,穿着套頭的休閒服,沒有化戲妝,兩根辮子編到頭頂,用黑髮卡卡住。她一口臨海普通話,聲音柔美,有湖水的味道,笑起來露出兩顆雪白的小虎牙,讓人覺得很好接觸。
父親和她老公駱老闆坐在台下聊天,我和她坐在戲台右側的廟門口聊天。我表明了來意,大意是我是一個寫作者,特爾喜歡越劇,不是來採訪,也不一定寫什麼,就是想來體驗一下戲班生活,如果單位或家裡臨時有事,我隨時會回去,我會儘量不打擾他們。
黑暗中,兩顆雪白的小虎牙說,你看得起我們,過來玩,我們當然歡迎,當然高興,很高興,你有什麼需要,儘管告訴我哦。
我眼前一下子浮現黛玉進府時熱情能幹的好嫂子王熙鳳的形象。
阿朱說,吃飯如果吃得慣,儘管跟着我們吃。被褥什麼的你自己帶會幹淨點,我們條件太差呵呵。
她又笑,戲台的側光映出她眼角淺淺的魚尾紋。
又聊了點別的,我問她生意好嗎?
她說,戲路還好,戲金不是很高。上半年做了200場,下半年也差不多,還好,也就是掙個工資錢,演員工資一天100到400多不等,賭博戲、亂七八糟的戲,我們不做的。也不是有多高的水平,有多高的收入,常年奔波,競爭厲害,要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很累。但我們戲班最難得的,是特別和睦,在一起十多年了,沒有多話的,很開心的,很多戲路是口碑好人家找過來寫戲的。
「寫戲」,即外鄉人過來邀請做戲、雙方商定劇目、戲金、時間、地點。
吉祥越劇團其實是一個家庭戲班。阿朱夫妻掌舵,爺爺搬道具,稱作「值台」,奶奶燒飯,阿朱和嫂子演戲,25歲的兒子負責燈光舞美和字幕。駱老闆個子高高的,壯壯的,雖是老闆,但看得出來什麼事情都找阿朱商量,他接到我文廣新局朋友電話後,也把我交待給了她。手裡卻一直拿着兩罐王老吉要我和父親喝。
爺爺仿佛是個隱身人,出入戲台搬道具像風一樣自由,被觀眾自動忽略。戲班裡,管戲服道具的「值台」或「大衣」是最辛苦的,有的終年睡在四處漏風的後台守夜。爺爺下台來就對我笑,將凳子讓給我讓我坐着看戲。
我之前擔心他們對我的到來有顧慮或反感,但戲班裡的每個人都很和氣,也沒有過分的熱情,只有阿朱25的兒子沒有笑容。
阿朱說,兒子說夏天過後他不做了。
那他做什麼呢?
阿朱說,我們讓他做,他還是會繼續做的,從小跟着我們到處走,很聽話的。
我從側幕看過去,看到了兒時的他和今夜的嘟嘟一樣,跟着戲班四處漂泊。突然想,多年後,嘟嘟一定不會記得今夜了,但還會喜歡看戲嗎?
住處
午後十二點五十分,雨停了。
阿朱在偏殿宿舍的水槽前搓洗着一大盆髒衣服,化着妝,裹着頭,穿着白色小衣小褲。
我問她,快一點了,你下午不演嗎?
她一把關掉水龍頭,邊擰衣服邊說,演啊,呀,來不及了哈哈哈。
她說着,將衣服往繩子上一搭一拍,小跑上坡,跑進廟裡,從戲台下坐滿老人的第一排前穿過去,緊跑幾步跳上台階,穿過樂隊,衝到後台,拎起早就擺放在那裡的藍色戲袍和相公帽,三下五下穿戴整齊,待她掛好無線麥克風,低頭套上高靴,從她公公手裡接過道具褡褳背上肩,沒怎麼停留就站到幕旁開唱了——
「三載同窗情似海,冬生難捨玉英妹。相依相伴情意深,未知何日重相會……」
聲音洪亮,氣息平穩,韻味十足,演的是《藕斷絲連》中的林冬生,套的是《樓台會》的曲。音樂過門後,她瀟灑地一個抬腳,高靴將戲袍輕輕一踢,便走出了側幕,走上了燈光耀眼的戲台。一個風流倜儻的小生,走進了老人們模糊的視線;而一個女子走進了古代,走進了另一種人生。
阿朱和她的姐妹們會演的戲多達一百多部,最駕輕就熟的就有三十多部,成竹在胸,才如此不慌不忙,信手拈來。
我亦步亦趨緊跟着她,最後在側幕驚住。眼前這個光彩奪目的人,幾分鐘前還在簡陋的住處吭哧吭哧地搓洗着一大盆髒衣服。
夜裡八點,潘香皺着眉頭,坐在床鋪上就着昏暗的燈光背唱詞,一個很舊的黃色筆記簿上,歪歪扭扭記着滿滿的唱詞。今晚,她演《雙龍太子》裡的包拯,戲份很重。
這是關帝廟最靠里的偏殿後一間約十多平米的屋子,三張床鋪分別用兩根長凳加硬木板搭起來,鋪着棉褥和涼蓆,沒有蚊帳,床上堆了些洗漱用品、化妝品和內衣。一張舊桌子是唯一的家具,擺着兩個巨大的化妝盒,兩盞沒有燈罩的檯燈見縫插針,就是她們的化妝檯。
一個很大的塑料桶,是拿來燒熱水洗澡的,用熱得快燒,廟裡沒有淋浴設備。
我說,我家很近,你們洗澡不方便到我家洗吧。
潘香笑,說,都習慣了。
牆角有一個電蚊香,靠牆有一張塌了的舊床,堆滿了鍋碗瓢盆瓶瓶罐罐,還有西瓜、桃子、楊梅。潘香說,是上個村子的戲迷和這個村子的頭說她們演得好,送來犒勞她們的。
俏俏削好一個桃子遞給我,並不叫我,只微笑着說,你吃。
我接過桃子,說,你們管自己忙哦,不用管我的。
一位70歲左右身材瘦小的婆婆正坐在另一張空床上吃蘋果,她是從清港芳杜跟過來的老戲迷,她常找她們玩,沒什麼好玩的,就是看看她們,還有三四個清港其他村裡的老太太下午來過,路更遠,回去了。
潘香眯縫着一千五百多度的近視眼,吃力地背着唱詞。別人演戲可以看戲台兩側的電子屏,她因小時候腦震盪耽誤治療導致弱視,全靠背下來。她身體也不太好,左腿膝蓋骨有畸形腫瘤,發作起來會很痛,演武打戲翻跟斗更痛。但如果不出來做戲,老公兒子上班去了,她一個人在家呆着沒意思,這裡有意思。
這間房,住了她、和她最要好的小生賽菊、和賽菊最要好的俏俏嘟嘟,還有當家小旦愛妃。賽菊家近,夜裡基本開車回家住,把俏俏母子也帶回家。
潘香說,我們幾個從來不分開的,別的戲班來挖牆腳,我們誰都不出去,我們已經是一家人。
她總是未開口先笑,眼神里透着孩子般的純真。
短短兩天,我已經聽到好幾次「一家人」了。在戲班裡,能成一家人,是特別難得的。
一百年前,中國第一個越劇戲班在嵊縣東王村出了娘胎後,不到兩年時間,剡溪兩岸的小歌班竟多達兩百多家。藝人們沿着三條路線流浪,一是從新昌、餘姚到寧波,二是從上虞、紹興、流動到杭嘉湖,三是從東陽、諸暨進入金華,他們像吉普賽人一樣,走到哪裡唱到哪裡,吃住都在廟裡殿前,和神祗睡在一起。身體上的苦在其次,被人看不起也是輕的,最怕的是在內主角配角間勾心鬥角,在外遭受地痞流氓欺壓。一百年來,戲班裡的人們聚散無常,更談不上親如一家,即使到了現在,也各有各的亂象,各有各的不易。
潘香將長發盤進發套時,微微翹起了蘭花指,無名指上一個玫瑰花形狀的金戒指,與包拯的形象反差很大。前一秒她還是一個女人,後一秒她就是一個男人。她說,我和賽菊約好,兩個人把頭髮都養長,然後剪下來,做成用自己的頭髮做的頭套,這樣就又方便又自然啦。
她站了起來,說,我快上場了,我要先去下廁所。
我也站起來,說,我扶你去吧。
她說,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啦,習慣啦,先戴上眼睛哈哈哈。出宿舍門,她往左,我往右。我回頭看到她大紅的燈籠褲、白色的斜襟小衣隱沒在暑汽蒸騰的夜色里。
五 小生
當我第一眼看見小生賽菊,仿佛又一次看見了多年前坐在我家三樓南窗下一筆一筆描着眉的「他」,看見了一輪冬日下午三四點鐘溫柔的太陽。
這是吉祥戲班在山後浦做戲的第四天下午。
這個潘香一天要念叨很多次的叫做「賽菊」的女人正坐在宿舍的檯燈下補妝,強烈的燈光將她臉上的細部暴露無遺。四十出頭的她看起來只有三十歲,化着小生的妝容,面部輪廓俊朗,五官精緻,眉毛和眼角均微微上揚,漆黑的雙眸異常清亮,身段苗條緊緻如處妙齡,黑色的蕾絲上衣、黑色的裙褲很飄逸。一個女子靜靜坐在一個極其簡陋的場景里一下一下描着眉,散發着一種攝人心魂的靜美。
賽菊話很少,只微笑着跟我打了個招呼,說,條來嬉啊,吃楊梅哦!
我說好的謝謝,你管自己忙哦。
她的聲音很潤朗,又帶一點點磁性,仿佛暗夜裡凝結了一層水霧的青花瓷。這個聲音讓我突然想起了另一個人,一個歲月深處曾經紅遍玉環每個角落的越劇名伶,一位耄耋老人。
俏俏把嘟嘟往潘香床上一放,俯下身子在塌床那裡翻找什麼。潘香已經化好包拯妝,抱起嘟嘟坐在自己的肚子上,一邊輕輕顛一邊哈哈笑。嘟嘟一點都不害怕她的臉黑,也跟着呵呵呵笑。
俏俏翻出了一個瓶子,自言自語說,再泡點苦瓜茶喝喝。
賽菊對着鏡子描眉,並沒有看她,說,今天別喝了,喝多了胃寒。
俏俏說,哦。聽話地放下了瓶子。
「勸妻休要淚淋淋……」
夜幕和黃梅雨同時降臨時,賽菊穿過夜色,走上後台,出場亮相。戲台在漆黑的夜色里,如同夜空洞開着一扇綺麗的天窗,走馬燈似地播映着天上人間的悲歡離合。今夜賽菊演的第一場是哭戲,《包公斬楊志平》中的韓世昌在病床上與愛妻話別。黑色的長髮垂下半邊,額上的汗珠、眼裡的淚水,在夜色中閃閃發亮,哀婉的唱腔在關帝廟的夜空中盛放、枯萎。
家鄉人將看戲叫做「望戲」,一個「望」字,畫出了人山人海中人們翹首張望的樣子。我像空氣一樣尾隨着她,望着她,也望着戲台下一張張條凳上坐着的幾十位老人,他們安靜如大殿裡的一尊尊雕塑,守廟人來喜站在最後一排。整個廟宇里,人神共看一台苦戲。
當我們望戲的時候,賽菊在自己的淚水和唱詞裡,依稀望見了許多逝去的歲月。
十年前,溫嶺江夏村。那天她演落難公子應天龍,用餘光向戲台下望去,如她所料,又看到了那個三十多歲的賣糕女人坐在第一排左邊的長凳上,痴痴地望着自己。她的身邊,仍然坐着那個十七八歲、眉清目秀、衣着整潔的傻子。他和她一樣,張着嘴,痴痴地望着自己。
淚水在她高亢哀婉的唱腔里紛紛墜落,人們紛紛起身,邊擦眼淚邊掏出幾毛錢、幾元錢扔到了戲台前。
一段詞唱畢,戲裡的「惡霸嘍囉」上台來,一邊叫罵一邊佯裝打她踢她。一根棍子眼看就要落到她身上時,突然被一個影子一把奪去——不知何時,台下的那個傻子已經躥上了戲台,漲紅着臉,撕心裂肺地嚎叫着,不要打她,不要打她!
他哭着叫着,用頭和身子去撞那些「惡霸嘍囉」。
賽菊趕緊從台上爬起來,戲班子人也都圍上來,勸他說這是做戲,是假的,是假的。
他躺在戲台上不肯起來,放聲大哭。
這時,坐在他身邊的那個三十多歲的賣糕女子跑上了戲台,一把摟過他,又一把拉過賽菊,讓他看她的臉、手,說,你看你看,沒有受傷,是假的,菊不是好好的嗎?
傻子呆了呆,突然笑了。爬起來去撿拋在台前的那些錢,撿完轉身捧給她,說,菊,給你,都給你。
賽菊搖手說不要不要,眼睛卻濕了。
多年後,比她大八九歲的賣糕女子也就是傻子的娘姨,成了她的至交,有了近親般的人情往來,賽菊結婚、坐月子、造房子、過生日,她都會送來點心、七八套衣服。娘姨家造房子、兒子結婚,賽菊也去,她跟着傻子叫她娘姨,其實心裡當她是親姐姐。
幾年前,玉環龍溪山里。那天她演《雪地打碗》中的孤兒周強,八歲因遭大伯母虐待逃出去討飯,是她的拿手戲。看戲的全是上年紀的老人,穿戴都很樸素,一段唱詞唱完,每位老人都起身,五元十元的,個個含淚送了一次又一次,足足送了六百多元。下台後,一位老奶奶過來拉住她哽咽着說,你演到我心裡去了,我和你一樣,從小沒爹沒媽,苦啊……
「討飯戲」是一個老傳統,一般去一個演出地都會演一場,不為圖捐錢,是圖彩頭,也最見功夫,演員動情,戲迷過癮。而同樣是《雪地打碗》這本戲,她在另一個村里演時,卻遭遇了恥辱。那天她剛唱頭一句「雙膝跪在大街前」,一個村幹部模樣的人就掏出果凍直接朝她身上砸。她氣極了,站起來不唱了,那人就叫囂着逼她唱,還要罰戲。淚珠在她眼眶裡打轉,卻說不出一句話來。戲班裡的姐妹衝出去跟他講理,最讓她感動的是台下的老人們全都幫着她們說,說他怎麼可以把她當成真的要飯的?!
賽菊不知道,在離山後浦關帝廟戲台的三百米處,曾經搭過戲台,鬧過罰戲。以前做戲不能唱錯做錯,錯了就要罰戲,輕的加演折子戲,如果做漏了情節叫「偷戲」,要重罰三天戲,戲班就要虧本。明張岱就曾描述過其時紹興演戲時「一老者坐檯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群起噪之,又開場重做」。
多年前,山後浦做戲,一個花旦演下樓的戲,按規矩要走13級,那天卻多走了一步。以前看戲的有很多年輕人,當時一群後生起鬨要罰三天戲,戲班頭子和做戲人都嚇壞了,趕緊請父親這個山後浦的老知識分子去說和。
父親被他們扶到戲台前的長凳上,站在耀眼的燈光下,說,鄉親們,戲班做錯了,是不對,但他們一不是故意的,二是小錯也已經認錯了,三呢也加演一段戲了。大家想想,我們到哪裡掙錢都難的,他們也很不容易的,大家就體諒體諒,好不好,和氣生財麼!
其中一個小伙不知道說了句什麼,一位老人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吼道,蘇老師都說了,你還要怎樣?快轉回家去!後生們也就散了。
如今,看戲的年輕人幾乎沒有了,老人們沒那麼精明也不計較,罰戲自然也就沒有了。但賽菊每一場都全情投入,更不允許自己出錯。她們來山後浦第一晚演的是《雙殺嫂》,沒下雨,來的觀眾多,紛紛叫好,第二天下午演《丞相試母》,觀眾反應又很好,地方上的頭聞訊很開心,買了幾十斤桃子、四個大西瓜送給戲班。賽菊忙得一口都沒吃,但心理上很滿足。她想,我就是戲裡的丞相施文青,觀眾喜歡這個戲,說明我演活了。
有那麼一兩分鐘,後台只剩下我一人。我忽然發現掛着皇帝帽的架子下的神位前點起了兩支紅蠟燭。我知道,又有老人「戲剎」了,也就是傳說的看戲走火入魔了,身體不舒服了,解藥就是到戲班後台點上蠟燭拜拜神仙老爺,來不了的就差人剪下一點皇帝帽的流蘇燒成灰喝了就沒事了。有用沒用不知道,戲班卻總是有求必應,讓看戲人圖個心安,就像故鄉人說的,高麗人參太補,邪關住了,要用蘿蔔解。
在後台,我不敢亂走亂動,隨便問話,怕犯了戲班的禁忌。小時候就聽說,不能問帽子重不重,不能問嗓子好不好,身體好不好,這些都關乎做戲能否順利,關乎他們的平安,因而外人寧可信其有。還比如,鼓板是樂隊的靈魂,打鼓板的師傅叫「鼓板佬」,他坐的地方叫九龍口,是戲台上最神聖的位置,其他人決不允許坐,更不允許觸摸鼓板。
此時,小旦愛妃上台,賽菊退到後台,從貼着一個「賽」字的戲箱裡取出一條綁帶綁上頭,側過頭對我笑了一笑,眼角還掛着一滴晶瑩的淚。
再過一個小時,戲散後,她會開車回到距離此地十公里的漩門灣大壩老鷹窠的家,那是一個靠海的小山村,大壩未築成時,傳說連飛鳥都飛不過去。到家後,她會煮兩碗面給自己和俏俏當夜宵,然後幫俏俏給嘟嘟洗澡,睡下,第二天中午吃了午飯再趕過來化妝。
這個在古代和現實之間自如穿越的女人,她在海邊的家是怎樣的?她的丈夫是做什麼的?在家裡,這個優雅神秘的女人是什麼樣子的?她對我這個一直尾隨着她的不速之客是怎麼看的?
多日後,我看到她在微信里這樣寫道:第四天下午演《藕斷絲連》,我演林天賜。下半場還在化妝,來了非常非常難得的貴客蘇滄桑老師。我們小小戲班迎來大作家,心情無比興奮[憨笑][憨笑]
然而,當時她那麼沉靜,甚至有點冷淡。
蘇滄桑,女,1968年出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散文學會常務副會長。畢業於杭州大學,現就職於浙江省作家協會。在《十月》《人民文學》、《中國作家》、《散文》、《美文》、《散文選刊》、《讀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文學作品300餘萬字,出版散文集《等一碗鄉愁》等多部、非虛構文學《守夢人》、長篇小說《千眼溫柔》等。曾獲「冰心散文獎」、「中國故事獎」、「首屆全球豐子愷散文獎金獎」、「琦君散文獎」等。多篇作品入選全國各類散文選集、散文年選、排行榜,並被應用於中、高考試題,入選各類教材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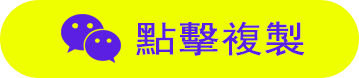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專業的情感服務機構真的不錯
求助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