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內容為虛構故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如我們所見,北戈是一個很好的名字,這名字使得他平白在一眾「二丫」「狗蛋」中脫穎而出,但這名字的所有者是個傻子,便陡然使得北戈降了一級。
更可惡的是這所有者長了一雙乳葡萄似的外國眼睛,這就導致了北戈成了一塊在糞坑裡沾了污穢的松石,人們便不得不為此扼腕嘆息了。
因此提起北戈的時候,人們總要將名字加個前綴,比如叔叔家的表弟管他叫「蠢蛋北戈」,在這些稱呼里只有北戈的母親是最溫柔的。

她時不時會捧起北戈的臉龐,一聲一聲地喚,「唉,我的傻瓜北戈呦,我的傻瓜兒子喲。」
當吐出這些話的時候,她總是一副憂鬱的模樣,就好像有人把住了她的脖頸,讓她僵硬着望着自己的兒子。
北戈被母親弄得發癢,因為她的手掌全是繭子。
北戈嘻嘻地笑了起來,他晃晃自己的大腦袋,眼睛再眨巴兩下,母親就放他出門玩了。
北戈出了大門,徑直往村頭的老槐樹下面去,他拖着鞋底,高高地抬起腳,發出啪嗒啪嗒的響聲。
有耳朵尖的孩子先聽到了,就禁不住跟旁邊的夥伴交頭接耳起來,片刻的時間,他們的喊聲就一浪高過一浪,「傻子!傻子!」
北戈看他們朝自己嬉笑,便爆發了一陣大笑,驚得樹上的喜鵲撲棱了翅膀,飛遠了。
其中一個男孩就不悅地撇撇嘴,低聲啐了一句,「喪門星。」
說着,他把沙包拋上榕樹叉,「傻子去撿,去撿啊傻子。」
這是他們常見的把戲,因此北戈不費什麼力氣就爬了上去,但這次的沙包拋得有些高,北戈就小心翼翼地踮起腳去夠。
「給,給。」
北戈手裡握着沙包,他滿頭大汗了,但仍舊笑着,那群孩子看到北戈的滑稽相,也促狹地笑。
「啊。」
當那群孩子再去望北戈的時候,北戈正單手吊在樹枝上,活像一隻長臂猿。北戈痛苦地閉着眼睛,右手卻還緊緊地攥着那隻沙包。
「好笑,好笑。」
一個孩子拍起了巴掌,所以孩子都跟起了風,這聲音引來了村長,他披着那件發白的外套,臉就像刻刀雕的,常年保持着一種嚴肅的神情。
孩子們見他來了,剛要拔腿跑,就被喝止了,「你們這幫狗崽子,一水的小混球。」
他一邊說,一邊把北戈解救下來抱在懷裡,摩挲着他發抖的後背。
孩子們垂着頭聽村長罵,他們不敢反駁村長,畢竟村長的脾氣極差,動不動就要打人。
「你們再欺負張北戈,我就像抽你們爹一樣抽你們,把你們抽成一幫小三孫子!」
這話給孩子抓住了漏洞,剛剛罵北戈的張陽笑嘻嘻地說,「張北戈?跟你姓的那個張啊?」
村長瞪了他一眼,「你們家的那個張!」
「呸!」男孩臉上頗有些怒氣地說,「我大爹早死了,他跟哪個姓的張?」
「再說你看他那個洋人的德行,哪點像我們張家的種?」
村長被男孩氣得說不出話,從他的臉頰上就能夠看出,他攢了不小的火氣,他剛要張嘴罵,臉色卻猛地一變,緊接着北戈就被丟到地上,「你也是個小混蛋,尿我一身!」
孩子們噗噗地大笑起來,只有北戈一臉茫然地盯着自己尿濕的褲襠。
北戈被村長抓着手,一步一踉蹌地跟着,從背面看,活像村長提了一隻半大的狗崽。
「北戈他娘。」
女人被村長一喊抬起了頭,她正用力去拔生鏽的鋤子上的木楔,旁邊還放着一盆沒漿洗完的衣服。
「正好。」村長粗魯地把北戈的褲子扒了,順手丟進那盆子裡,他攆着北戈去換內褲,然後蹲下幫女人修理起鋤子,鐵屑沾滿了他整個手掌,他咂了咂嘴說,「這得有好幾年沒使了。」
「嗯,長生死了以後,就沒人使了。」這話使兩個人雙雙陷入沉默,村長利索地把女人新買的錚亮的鋤頭安上,直起腰來長吁了一口氣問,「怎麼今天翻出來了?」
「明天下地。」女人停頓了好一會兒才接着說,「不然養活不了北戈。」
「啥?」村長先是浮現出一絲驚訝,隨後他的眉頭越皺越緊,說出的話也頗為憤懣,「長生留的錢花光了?」
女人的臉由被指責後的漲紅變成了一縷哀愁,「老二說要給小陽準備上大學的錢。」
「就他?」村長從鼻子裡哼出一聲,「那錢是長生留給北戈的。」
提起過世的丈夫,女人怔住了,而後滿足地笑了笑說,「他收留我們那麼久啦。」
這時北戈探出了腦袋,他眯起眼睛的樣子,像極了他的養父。
因此北戈的母親想起自己大着肚子回村的時候,只有那個男人接納了自己,甚至為了北戈上戶口,他毫不猶豫地娶了自己。
想到這,女人又心酸地笑了,「他是一個偉大的人。」
村長原本要說些什麼,但他看見了北戈,到了嘴邊的話又換了,「說起上學,你也該讓北戈去學校了吧,還能一點書不念?」
「我天天教他。」
女人不知道從哪淘換了一本英語書,書頁的邊緣有些皺巴,就像一條哈巴狗似的。
女人的那點英語還是北戈的生父教授的,儘管誰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女人對英語單詞認識的並不多,但所幸北戈並不聰明,因此都一年多了,母子倆的學習進度還停留在二十六個字母上。
「你就一輩子讓北戈說洋人的話!不識好歹!真是不識好歹!」
村長被女人的固執氣壞了,他提高了嗓門,可不巧,他呸出的唾沫回嗆到嗓子眼裡,引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
北戈見狀去家裡拿了一杯水,他的綠眼睛在此刻格外深透,裡面有一股單純的光射出來,這使得村長不忍心再苛責他的母親了,只撂下一句話,「明早七點把北戈送到學校,我在那等。」
村長甩了甩被尿濕的袖子,那袖子已經有些發乾了,顯現出一股難聞的尿騷味。
北戈看着母親,拍了拍自己的小肚皮說,「餓了。」
母親又恢復往日裡柔和的神情,她把手指在衣服上擦乾淨了,才走去廚房給北戈端出了一碗麵條。
麵條是提早下好的,有些坨了,但北戈依舊吸嘍吸嘍地吃了起來。
這是北戈的習慣,總要在午飯後,結束玩鬧時再吃上一頓,才能安心地去睡午覺。
女人看着北戈進屋了,才若有所思地盯着鋤頭看了一會兒,而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第二天一早,北戈被送去了校門口,他背着母親連夜趕製的書包,眼神懵懂極了,他的母親正扛着鋤頭跟在他身後,可即便是這樣,孩子們看向北戈的眼神依舊是毫不留情的厭惡。
甚至有些大膽的,還會在北戈母親面前轉悠一圈,刻意去背一首複雜的古詩來嘲笑說話都不是很利索的北戈。
「張陽,你大娘來了,是不是找你啊?」
和北戈同村的男孩一眼就看見了他們母子倆,因此忍不住打趣一起上學的張陽。
張陽推了同伴一把,極為厭惡說,「啥大娘?」
偏巧北戈的母親看見了他,跟着笑了笑。
同伴的嘲笑聲陡然擴大了,張陽漲紅了一張臉,轉身跟同伴扭打了起來。
兩個男孩的打架沒有章法,只是在地上滾來滾去,激起了一片塵土。
北戈看見了他們,以為是什麼遊戲,也入迷地看了起來,直到被母親提醒後,他才後知後覺地去拉架。
北戈的力氣很大,輕易就把兩個男孩分開了,因此這兩個男孩換了打架對象,默契地把北戈摁倒了。
「我看你們是欠揍了!」此時村長的一聲恫嚇讓兩個男孩收了手。
他們火速爬起來,顛三倒四地往學校里跑去,村長余怒未消,突出的青筋拉扯着他脖頸上老態的皮膚,使得村長看起來像一隻倔強的鬥雞。
這時北戈也爬了起來,他拍了拍被弄髒的書包,很抱歉地看向母親,女人看着北戈與他生父如出一轍的表情,徹底失了神,直到村長要領北戈進去,她才低頭囑咐北戈說,「要聽話,好好吃飯,團結同學。」
北戈看有這麼多孩子,高興不已,他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興奮,只從嗓子裡發出嗷嗷的聲響,引起了一陣側目。
北戈雖然已經十三歲了,但他沒學過知識,被學校安排在了一年級。
「張村長,我領他進去了。」班主任對牽着北戈的村長如是說道,她早就聽說了北戈早晨在校門口引起的混亂,因此頗為憂心忡忡地問,「他沒問題吧?」
「那有啥問題?」村長瞪了一眼老師,但他那一貫的如刀刻的表情也顯現出愁容,畢竟張長生臨死前,已經把北戈母子託付給了自己。
想到這,他又瓮聲瓮氣地說,「張北戈要是被欺負了,你看我找你算賬。」
老師只好無奈地點點頭,果不其然,北戈那雙綠眼睛在班級里引起了軒然大波。
孩子們有的好奇,有的害怕,甚至膽子小的還尖叫了起來。
北戈在這期間望了一眼站在門外的村長,偷偷地咧開嘴,露出了一排整齊的小牙。
村長滿意地點了點頭,外面的陽光照在他身上,金色的光芒使得他的表情也柔軟了起來。
他伸手示意老師正在講話,北戈這才把臉調過去,但他依舊是笑着的。
村長這才放心離開了,他的步子較平日裡輕了許多。
「張北戈,你坐最後面那個空位去。」
最後一排的位置多數空着,只有一個男孩趴在那裡睡覺。
北戈的第一節課就是數學,他從書包里掏出村長給他借來的舊書,全數擺在課桌上。
「這本。」那男孩討厭北戈嘩啦嘩啦翻書的聲音,於是從那些書里拿出了藍色的數學書,遞給了北戈。
上課鈴響了,數學老師一進門就看見了空位上的北戈,因此他開口問,「後面那個新來的,你叫什麼?」
北戈突然被一堆視線包圍着,他無措攥緊了拳頭,下意識地看向那個幫助了自己的鄰座。
那男孩豎着一本數學書,把頭埋得低低的,肩膀還跟着一抖一抖的。
北戈便有樣學樣地跟着趴下了,這激怒了數學老師,他怒氣沖沖地走下來,伸手用力揪住了兩個人的耳朵。
「我看看你們倆在這幹什麼!」男孩吃痛,跟着站了起來,而他正在看的漫畫書被抖了出來。
「上課讓你來看小人書的?」
男孩低着頭,趁着老師翻看漫畫書的工夫狠狠白了北戈一眼。
老師把漫畫書捲起來,分別砸了北戈和男孩一下,而後他看向北戈,似乎被那雙碧綠的眼睛嚇到了,只嘟囔了一句:「小洋鬼子。」
之後他覺得失去了顏面,讓兩個人貼着牆罰站才回到講台。
男孩整節課都在為自己的漫畫書長吁短嘆,因此下課鈴一響,他就來找北戈算賬了。
「你賠我書。」
北戈並沒有弄明白怎麼回事,還沒等他說話,就男孩提醒說,「李亮,你最好離那個人遠點,小心把你傳染成綠眼珠子。」
短短一節課的時候,北戈的同學們就決議與他劃清界限,雖說是好心提醒,但在李亮聽來顯得格外刺耳。
他撇了撇嘴,北戈比他高整整一個頭,因此他的小短手只能夠到北戈的肩膀,那模樣看起來就像小丑在努力地將自己綁在一根柱子上。
「我就喜歡和小洋鬼子玩怎麼了?綠眼睛多酷啊,一群土老帽。」
「餵。」他看北戈沒反應,就用力撞了撞他的肩膀,「你以後就當我朋友吧。」
這話一出口,他驕傲地抬高了頭,雄赳赳地坐下了,又從書包里掏出了一本漫畫書。
北戈看着他,友好地笑了笑,他從書包里掏出一盒村長塞給他的餅乾遞給男孩,男孩也不客氣,吃得整個書桌都是餅乾渣。
北戈放學的時候,村長在校門口等,一眾成群結隊回家的孩子裡,北戈顯得格外特殊。
李亮則盡心盡力地做身為朋友的職責,他在北戈耳朵喋喋不休地說着自己對各科老師的認識,最後才壓低了聲音說,「我明天要去把漫畫書偷出來,到時候你給我望風。」
北戈不知道望風什麼意思,但他還是點頭答應了。
兩個小夥伴在校門口分手,村長一如既往地牽緊北戈的手,走了許久的路,他才貌似不經意地開口,「今天上課咋樣?」
提起這個,北戈的神采就像一隻飛舞的小鳥,一刻也不肯歇腳。
因為李亮並不捉弄他,還和他一起玩丟沙包的遊戲,村長見此,心終於踏實了,他臉色也逐漸變得紅潤,就像喝了一壇陳年的好酒。
北戈的母親特意為兒子準備了好飯,她煮了兩斤紅燒肉,和整整一鍋的白米飯。
這香氣也引來了北戈的二爹一家,他們鮮少來到北戈家,而一家三口整整齊齊地來更是過年都看不到的光景。
「呦,村長你人真好,還管接送孩子,以後小陽你也一起接了吧。」
村長聽着北戈二娘的混賬話,沒說話。
這婆娘的肚皮里又落了一粒她男人的種子,此時已經有些顯懷了。
「北戈他娘,明早按時把張北戈送去上學。」
「好。」
簡短的對話後,村長離開了北戈家,北戈放下書包,同母親一起把飯拾掇到桌子上。
飯吃了一半,北戈二爹的眼睛在他大嫂的身上轉了個來回,才笑眯眯地說,「小陽你以後在學校要幫着哥哥。」
「呸。」張陽絲毫不掩飾自己的厭惡,只是話沒說完,就被他爹踹到了炕底下。
「你瘋了!」
女人的尖叫聲跟李陽的哭泣混成一片烏雲,壓得北戈的母親喘不過氣。
在這混亂里,北戈依舊不緊不慢的,吃得滿嘴流油。
等把這一家子送走後,已經晚上九點了,北戈在母親低沉的歌聲中昏沉沉地睡去。
北戈的母親輕手輕腳地去收拾東西,而後她從錢袋裡數出一百塊錢,準備第二天送去給她做裁縫的哥哥,請他給北戈做身新衣服。
然而還沒等她走到哥哥家,北戈就在學校里出事了。
據老師說,北戈在學校調戲了一個高年級的女孩。
等他趕到學校的時候,北戈已經被拉到辦公室批評了一輪,北戈垂着頭,他不知道怎麼說清來龍去脈,只好聽着對方「小流氓」地罵。
有老師看不過眼說了句話,就被對方家長引到了學校教育上,「咱這是什麼國際大城市?還收洋鬼子?」
校長瞪了眼那個老師,嫌他多事,又安撫似的說,「小孩沒爹,教育肯定是有欠缺,但這屁大點的孩子,也沒啥壞心眼。」
「屁,他長大了也是個蹲笆籬子的!」
一直在門外偷聽的李亮忍不住了,「蹲笆籬子」可算是這裡最惡毒的詛咒了,因此他跳起來喊,「你咋不說你閨女以後肯定住醫院呢。」
李亮替北戈有些委屈,「別人都笑話她,就北戈給她擋着,我看你們才是一家流氓。」
「你少在那胡說八道!你以後也是個蹲笆籬子的!」
女孩的家長並沒因李亮的話感到一絲羞愧,反而罵得更難聽了。
李亮被老師強制扭了出去,在出去之前北戈的母親到了,她手裡還攥着那一百塊零錢,「北戈怎麼了?」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兒子,北戈的臉色慘白,他就像麵塑的小人,被人輕輕一捏,就四分五裂了。
北戈在校長的示意下被帶了出去,先他一步出來的李亮很有義氣地拍了拍胸脯說,「我給你作證!」
然而學校並沒有給他這個機會,當天的事情是以賠償一百塊,以及北戈的暫時休學為落幕。
當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女人抱住北戈,嘴裡又吐出了熟悉的話,「我的傻瓜北戈呦,傻兒子。」
過了好一會兒,她又摸着北戈的大腦袋笑了笑,「你真是個偉大的人。」
說完,她給北戈唱了一首之前沒唱過的歌。
那是一首外國的歌謠,即使在北戈睡着以後,她的歌聲依舊沒停。
那蜿蜒的歌聲仿佛溫暖的海水,輕輕托起北戈,撫慰着他那顆受傷的心靈。
第二天一早,村長就再次登門了,他身上還有微微的濕氣,一看就是冒着大霧走來的。
「我聽說了,今天我就去找校長,讓北戈重新上學。」
「不用了,」女人看了一眼在翻課本的北戈,搖了搖頭,「他上學校,受欺負。」
深秋的時候,北戈的二爹又上門了。
他手裡拎着半口袋的面,身後還跟着他的兒子,張陽。
「嫂子,送你們點面。」
趁女人把面倒進麵缸的時候,他沖自己的兒子使了個眼色,張陽不為所動,只默默地伸出了兩根手指頭。
男人點了點頭,張陽才得意地接受了父親的任務。
北戈正在往竹竿上晾濕衣服,也許是受了學校那個女孩的影響,北戈這些天很少出門,村裡的孩子們找到了秋收的樂趣,也徹底把北戈遺忘了。
張陽換上一副笑臉,他引誘北戈說,「我們一起去打沙包啊,我們一起玩。」
北戈並不為所動,張陽臉上浮現出一絲不耐煩,但他隨後被父親嚴厲的眼神嚇住了,好脾氣地說,「我叫了李亮一起。」
隨着兩個人出了門,北戈的二爹臉上浮現出猥瑣的笑容,他輕手輕腳地關上了院門,上好了門閂。
北戈跟着張陽走了不短的路,最終他停下了腳步,遲疑着問,「我們去哪?」
他的綠眼睛裡倒映出張陽嘲弄的笑容,那笑容過於成熟,實在不該出現在一個孩子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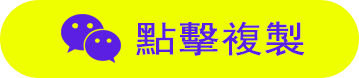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服務特別好,而且給人的感觸也挺深的,真的可以的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