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內容為虛構故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1
有人說過,一個合格的前任就應該像個死人一樣。然而在和江攬月分手的第九個月,俞輕舟發現她「詐屍」了。
並且炸得不合時宜,因為他們是在寺廟裡重逢的。

看到她的那一刻,俞輕舟就着滿地浸泡了春雨的落花,杵着掃帚愣在原地,表面穩如泰山,內心卻慌作傻狗。
而比他更慌亂的,是站在不遠處同樣僵化當場的江攬月。
眼下適逢穀雨節氣前後,南城斷斷續續飄着春雨,她撐着一把墨綠色的圓傘,透過飄渺的雨絲兒朝他望過來。
目光觸及他那光溜溜的腦袋以及合身的僧袍,她臉上的神色變得尤其複雜,向來溫潤的眼睛裡露出幾分若隱若現的不解和慌張。
腳下更是像生了根似的,再也挪不動半寸。
同事往前走了好些距離,才發現江攬月沒有跟上來,於是停住腳步,回頭朝她喊了一聲:「小月亮,你發什麼愣,趕緊跟上呀!」
江攬月被同事這一聲招呼給喚回了神智,她想起今天是陪同事過來廟裡上香的。
前陣子同事過完生日,正式踏入了三十歲大齡單身女青年的行列,家中二老催婚的節奏突然就被拔快,幾乎每個周末都給她安排了好幾場相親。
可相了那麼多次,紅鸞星硬是按兵不動。
無奈之下,飽受相親摧殘的同事病急亂投醫,聽了單位一位熱心腸姐姐的建議,趁着假期便拉了江攬月到郊區的南山寺來求姻緣。
想到此處,江攬月壓下滿腹疑惑,把目光從俞輕舟身上撤了回來。她小跑跟上同事的步伐,沉默了半晌,突然開口問道:「這個廟裡的姻緣簽是不是真的很靈?」
靈到她還沒有開始許下願望,就已經先和俞輕舟再次見了面。
同事沒發現江攬月的不對勁兒,半信半疑回道:「大概吧,貌似很多人都說挺靈驗的。」
江攬月點了點頭,沒再說話。
她滿腦子想的都是剛才小和尚模樣的俞輕舟,為什麼他會穿着僧袍?為什麼他會剃了光頭?為什麼他會在廟裡掃地?越想,心裡疑惑越大。
和同事走到寺廟的主殿門口時,她還是決定回去找一個答案,於是頓住腳步:「我還有點事,你先進去,我等會兒再過來。」
說罷,也不等同事回答,便順着來時路飛快地往回走。
幸好,俞輕舟還在那裡掃地。只不過這時他背對着她,所以並不知道她又回來了。
江攬月稍微平復了一下怦怦跳的心律,慢慢走近,語氣儘量平緩地出聲喚道:「俞輕舟。」
俞輕舟再次怔了一瞬,回頭,對上她那雙溫潤的眸子。他許久沒見她了,這半年的思念如同野草瘋長。
雖然還在生她的氣,但想到倆人現在好不容易才碰到一回,所以他打算瀟灑大度一點,跟她心平氣和說兩句話。
只不過他不知腦子怎麼的就抽了筋,打好的理智腹稿最後變成了脫口而出的否認:「施主,小僧法號慧緣。」
話一出口,俞輕舟就恨不得立刻刮自己兩個大耳光,媽的,這說的都是什麼屁話?
果然是在廟裡靜養的這段時間太閒了,他就不應該看那麼多狗血連續劇。
江攬月不知道俞輕舟的心理活動這麼豐富,聽着他一本正經的回答,她驀地就被噎住了,好一會兒才找回自己的聲音,不敢置信地問道:「你,出家了?」
俞輕舟騎虎難下,琢磨了半晌,然後給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我現在住在廟裡。」
2
雨勢漸漸大了一些,看到俞輕舟沒有回去的意思,仍在勤勞地掃着地上的落花,江攬月識趣地沒有再去追問,而是高高地舉起手,替他撐着傘。
同事求完姻緣簽折回來時,看到的就是這麼一幅畫面。那倆人之間的氣氛,靜默中帶着一絲詭異,詭異中又帶着幾分和諧。
江攬月的注意力全在俞輕舟身上,跟着他小步挪動,不捨得讓他淋一點雨,自然就沒有注意到身後滿臉震驚的同事。
還是俞輕舟眼尖,瞥見了不遠處的那個身影,他停下手上的動作,好心提醒道:「你朋友在等你。」
順着他的目光看過去,果然看到了一臉見鬼的同事,江攬月抿了抿唇:「那,我先回去了,下次再來看你,可以嗎?」
說完,她把傘塞到他的手裡,轉身往同事方向跑過去,留下俞輕舟握着那把傘,久久不能回神。
從南山寺回市區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江攬月一坐上副駕駛就開始閉目養神。
而同事憋了十分鐘,到後面實在是憋不住了,便誠惶誠恐地問出了心中的疑惑:「小月亮,你該不會是看上剛才那個小和尚了吧?」
江攬月突然睜開眼睛。
「雖然那小和尚看起來是挺俊俏的,但人家是出家人,你可不能亂來啊!咱們要有道德底線,你如果想談戀愛了,姐姐趕明兒給你找一個合適的,六根不淨的……」
同事仍在絮絮叨叨,看樣子,像是十分害怕江攬月誤入歧途。
江攬月覺得再不解釋的話,她怕是要被念叨一路,因而適時打斷了同事的話:「他是我的初戀,我倆差不多在一起五年,幾個月前才剛剛分的手。」
信息量太大,同事一下子反應不過來,安靜了片刻,她才試探性地開口:「所以,你們分手之後,他就看破紅塵了?」
「不知道。」
這說的是真話,江攬月的確不知道俞輕舟為什麼會一身和尚模樣出現在寺廟裡。當初他們大吵一架分手後沒多久,她就在酒吧里聽到了趙硯書那行人提起俞輕舟被公司外派到國外的消息。
她雖是心中有愧,雖是意難平,但相隔千山萬水,最後還是不了了之了。
聞言,同事不由自主想起了剛才那個詭異又和諧的畫面,再次詢問:「那你現在什麼想法?還喜歡他?」
這話把江攬月給問住了,她垂下目光,一下就看到了自己光潔的手指,那上面原本有一枚戒指的。
她覺得腦子有些重,就像被水浸泡過的棉花,沉甸甸的,讓人一陣壓抑。
她記得以前在一起的時候,她跟俞輕舟說過「我喜歡你」這四個字。
但後來倆人分手時,他生了好大一通氣,像個炸毛的小獸,一直在控訴她沒良心。
他說:「江攬月,原來你一點都不喜歡我。」
3
江攬月認識俞輕舟,其實純屬巧合。
那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情了,那時的江攬月還在榕城念大二,而俞輕舟是隔壁學校金融系的大帥哥,跟她同級,但沒有交集。
然而就是兩個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後來因為談敏真和趙硯書的緣故,碰到了一起。
談敏真是江攬月的室友,倆人說不上很合得來,但相比外人而言,總歸多了一層同住一個屋檐下的感情。
江攬月不知道談敏真是在哪裡認識的趙硯書,但在宿舍里聽她提起過很多回,甚至還信誓旦旦地說過要拿下他。
對此,宿舍的其他姑娘只當她是犯花痴了,沒當一回事。
直到某一天,談敏真來找江攬月,請她一起到隔壁學校去看籃球賽。
江攬月本來不想去,但耐不住談敏真的央求,最後還是答應了下來。也是那一次,她在球場上,看到了與賀程長得七分相像的俞輕舟。
然後,她聽見了自己胸腔內響起了擂鼓聲,咚咚咚,一下又一下,那是心動的聲音。
瞧着她出神的模樣,談敏真熱心腸地給她做了科普:「那個穿15號球衣的男生,是趙硯書的髮小,好像叫俞輕舟。」
江攬月點頭致意,剩下來的時間,她異常認真地看完了整場球賽。
球賽結束後,談敏真過去給趙硯書送水,其實她買了一箱水,但只拿了一瓶過去。其他隊員大概是見過談敏真的,所以對她的厚此薄彼紛紛起鬨,俞輕舟笑了笑,一手拖了一個貧嘴的就往球場邊上走。
江攬月坐在那箱礦泉水旁邊,等俞輕舟那群人嬉笑着走近時,她從箱子裡拿出水,一個一個遞給他們。
俞輕舟接過水,道了聲謝,瞧着她眼生,又問了句:「你是談敏真的朋友?」
「嗯,室友。」
聞言,他笑了笑,眉眼彎成一個好看的弧度:「其實我挺欣賞談同學的,一般人沒有她這個毅力。」
「啊?」江攬月一下子沒反應過來他說的是什麼,直到順着他的目光看過去時,才後知後覺明白到俞輕舟指的是談敏真在追趙硯書這件事情上毅力可嘉。
沉默了一會兒,她問:「你朋友為什麼不喜歡她?」
聽了這個疑問,俞輕舟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擰開礦泉水瓶的蓋子,咕嚕咕嚕灌了大半瓶水,剩下的半瓶倒在手裡洗了把臉。
隨後在她旁邊的台階坐下,像個情感大師一般,睿智開口:「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哪有那麼多為什麼?倒是你,有空勸勸談同學,做人不要一根筋,有些事情強求不來。」
說到這裡,他側頭看她,眼睛亮晶晶的。發梢滴着水,不知是汗水還是剛才的礦泉水,再加上皮膚白皙,與春日的陽光彼此相照映,他整個人看起來好像在發光。
在那一瞬間,江攬月似乎在他身上看見了賀程的影子,眼睛猝不及防地熱了熱,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4
那天回去之後,江攬月晚上睡覺做了個夢,夢到了許久不見的賀程,那個與她一起長大,但卻來不及和她一起變老的青蔥少年。
她似乎知道那是夢境,知道他走了之後就不會再回來。所以她努力地追着他跑,想要去拉他的手,可是她再怎麼努力,也仍然夠不着,他們之間好像隔着洪荒,被衝散得越來越遠。
半夜醒來,她出了一身虛汗。
第二天早上沒課,江攬月想了很久,最後獨自去了隔壁的財經大學。
籃球場有不少人,一部分是在上體育課的,還有一部分是三五成群過來玩的。江攬月往人群中看過去,但遺憾的是,她並沒有找到俞輕舟的身影。
接下來的時間,她幾乎每天都會抽點時間過來轉一圈,不過大多數時候都是無功而返,只有運氣好些的時候,才能在球場上看到那件熟悉的15號球衣。
一開始,俞輕舟看到江攬月出現並沒有什麼過多反應。但後面,他發現她似乎是每天都過來,便多留了幾分心。
一起打球的隊友也注意到這個情況了,跟他打趣道:「也許人家是特地過來看你的呢!」
「別瞎說!」
中場休息的時候,俞輕舟過去跟江攬月打招呼:「你喜歡籃球?我好像經常看到你來看籃球賽。」
「我過來散步的,剛好累了就坐下歇一歇。」
這理由蹩腳得很,誰天天散步散到別人的學校去,還能掐準時間掐准地點停下來歇息的?
俞輕舟不信她的說辭,只不過人家不想說,他也不方便追問。
彼此沉默了會兒,期間有羞澀的姑娘過來給俞輕舟送水,他沒有接,不過十分禮貌地道了謝。
江攬月在一旁靜靜看着,在她看來,俞輕舟屬於那種讓人很容易就會喜歡上的少年,熱烈,明朗,真誠。
她也不例外,因為她也喜歡俞輕舟。
打發走了追求者,俞輕舟回頭,猝不及防撞入了江攬月那雙清潤的眼睛裡。跟旁人熱烈的目光不一樣,她的眼神明明純澈坦蕩,但卻偏偏跟長了鈎子似的,能把人鑊住禁錮在裡面。
沒來由的,他臉上燙了燙,隨後匆匆挪開視線。
不明所以的江攬月從旁邊的購物袋裡翻出一罐還沒有開封的冰鎮可樂遞過去,聲音輕柔:「你喝嗎?」
慌亂地接過,俞輕舟只覺心跳莫名快了些,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了隊友跟他開的玩笑,然後滿腦子開始循環播放起「也許她是來看你的呢」這句話來。
沒來得及道謝,就幾乎是脫口而出一句:「你該不會是來看我打球的吧?」
話音落地,臉上已經酡紅一片,懊惱得恨不得咬舌根。
瞧着他的模樣,江攬月愣了愣,反應過來後直接拉開了汽水的拉環,再次遞到他跟前,佯裝淡定地回答道:「你終於看出來了?」
那一刻,好像風動了,又好像是心動了。
俞輕舟覺得自己應該說些什麼,但這會兒他的思緒已經亂飛,一肚子話塞到了喉嚨尖,愣是吐不出來,最後只好頂着一張大紅臉,默默接過她遞過來的可樂。
江攬月低低笑了一聲,隨後低頭看了一眼手錶,語氣仍舊輕柔:「我要回去上課了,明天再來看你打球。」
5
回到市區之後,江攬月沒有回家,而是拜託同事送她去了酒吧街附近。
「借酒消愁?需要姐姐陪你嗎?」同事擔心她想不開,畢竟前男友出家這種事,概率太低了,不是誰都能遇上的。
江攬月搖搖頭:「不用,我只是過來找個朋友。」
得到她再三保證沒事之後,同事先回了家。
天色還早,街上比較冷清,江攬月往前走了一段路,最後停在「星期八」酒吧門口。
那是俞輕舟和趙硯書合夥開的酒吧,以前還和俞輕舟在一起的時候,她來過幾次,裡面的服務員都認識她。
推門進去,燈光昏暗。
「不好意思,我們還沒營……誒,老闆娘?」
服務員小高認出她來,突然拔高聲調喚了一聲,江攬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你們趙老闆在嗎?我找他有點事。」
「硯哥出去了,要不我幫你打個電話問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好,謝謝。」
江攬月在酒吧等了一個下午,等到趙硯書回來的時候,已經接近傍晚了。
看到她的出現,趙硯書似乎並不覺得意外,施施然煮了一壺熱水,給她泡了杯清茶,這才終於開口:「我們酒吧有規定,不能賣酒給你,請諒解。」
江攬月酒精過敏不能喝酒,第一次來酒吧時,不知情的趙硯書給她倒了杯雞尾酒,入口就是一口清冽的甜意,她當成飲料喝了兩杯,回去之後,毫無意外地出了一身紅疹。
後來,俞輕舟制定店規的時候,就多加了一條:凡是江攬月過來,所有人都只能給她倒牛奶或者茶水。
想起舊事,不由得讓人感到一陣唏噓。
江攬月不想跟趙硯書敘舊,抿了口熱茶,便直接開門見山地說道:「我今天在南山寺見到俞輕舟了。」
聞言,趙硯書倒茶的動作一頓,再抬眸時,眼裡多了一抹淺淡的笑意。
看他沒有開口的意思,江攬月繼續問道:「之前我無意中聽到你們說他出國了,後來呢,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現在為什麼會在廟裡?甚至還,還穿着和尚的衣服。」
趙硯書並沒有給她答案,而是反問了一句:「你捋清楚了嗎,你真的喜歡他嗎?」
江攬月沉默。
「如果不是真的喜歡他,那就請江小姐不要再打擾我的朋友了。」
——
人有時候是很難看清楚自己的內心的,只有分開了,失去了,才後知後覺地恍然醒悟,自己最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江攬月突然想起自己追俞輕舟的初衷,算不得純粹,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可恥的。
那時在球場見了他一面,覺得他和賀程長得很像,於是便用些笨拙的法子,開始時不時在他面前晃。
後來,俞輕舟真的眼熟她了,有些什麼活動也會叫上她一起,倆人的關係才慢慢靠近。
記得那年放暑假的第一天,新聞出了晚上會有流星雨的預告,有人便提議到山上露營。
準備妥當,於是一行人浩浩蕩蕩上了山。
入夜之後,山上的溫度漸漸降了下來,風也有些大,涼颼颼的。圍着篝火吃飽喝足,大部分人便把等流星雨這回事拋到了九霄雲外,紛紛鑽進帳篷里取暖了。
江攬月不想回帳篷,安靜地在一旁收拾殘局,而俞輕舟則在不遠處搗鼓那架特地租來的天文望遠鏡。
沒多會兒,他把鏡頭對準了她。
她嗔笑提醒:「星星在天上。」
「但是月亮在眼前。」
少年的心思坦蕩而赤誠,表達愛意的方式卻含蓄而內斂。
那一刻,她仿佛在俞輕舟的眼裡看到了流星雨。
6
倆人在一起之後,俞輕舟稱得上是二十四孝男友。
陪江攬月泡圖書館,陪她上大課,有球賽必報備,不接別的姑娘遞的水,還把她的名字拼音縮寫印在了球衣上面。
並且時時刻刻把「我有女朋友」五個字掛在嘴邊,天天在趙硯書那些孤寡單身汪面前「月亮長月亮短」地嘚瑟。
一開始,江攬月覺得尷尬又羞澀,但時間長了,臉皮也被他修煉得差不多厚了。
畢業後,俞輕舟回了南城,一邊進了沈氏幫沈家的忙,另一邊又跟趙硯書開了家酒吧,偶爾搶人家樂隊主唱的麥克風過一過唱歌的癮,日子過得倒是逍遙自在。
而江攬月是跟他一起過來南城的,在電視台找了份工作,有時候忙起來三餐也顧不上吃。
俞輕舟怕她熬壞身子,後來便直接搬進了她的出租屋,負責起她的一日三餐。
如果沒有意外,在俞輕舟的計劃里,他應該是他們那群朋友里第一個結婚的人。
只不過,計劃一直都是趕不上變化的。
後來,俞輕舟無意中發現了一張江攬月珍藏起來的照片,頓時覺得整個人跌到了冰窟里。
那是一張合照,照片裡的江攬月笑得很是燦爛,而站在她旁邊的男孩,長了一張與他有着七分相似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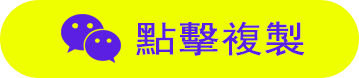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這個真的給我們很多幫助,特別是對愛情懵懂無知的年紀,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