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玉琪
第四次,還是第五次?

林文文已經不記得這是第幾次晉升失敗。她有點麻木了。
3年前,林文文加入這所互聯網大廠,成為一名前端開發程序員。她以為,這是人生新開端,還定出下一階段的目標:先在職業上獲得晉升,再花一年完成結婚、生娃等規劃。
但,「我埋頭苦幹,拿了不錯的績效,然後晉升掛掉,調整心態繼續下一個輪迴」。
看着以前帶的新人職位都比自己高,林文文很挫敗。「就好像你追一個人追了很久,但是他不拒絕你,也不主動」,像是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
在一個男女比例接近8﹕2的行業里,學者孫萍從2016年開始見證着女程序員如何試圖突破性別邊界,又如何陸續轉崗、轉行、回歸家庭。
因為性別、婚戀、生育,以及這個崗位刻在基因里的男性氣質,女程序員要比男性更能熬夜加班,更能忍耐和等待,要抹去性別特徵,活得比男性更像男性。
「在這個『吃青春飯』的行業里,最後能堅持下來的人很少。」孫萍說。
圖源:視覺中國玻璃天花板
林文文所在大廠的晉升機制是這樣的:每個部門都有一定的晉升名額,由部門領導對員工進行考核,決定晉升人選,考核沒有量化的標準,「相當於部門裡分豬肉」。
同樣的晉升渠道,同組的男同事只需要一兩次就過了,而自己屢屢失敗。她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工作上能力不能勝任,大可以指出問題所在,甚至讓她背鍋走人;如果能力勝任,為什麼晉升總是輪不到自己?
她不是沒和領導溝通過。領導覺得是她「運氣不好」,上次說是業務差一點,這次告訴她技術差一點。每一次,領導都會極力挽留她,並跟她保證「下次一定」。
「下次努力就可以了。」領導還會用其他女性同事晉升的例子安慰她,「你看那個誰誰誰不也很優秀,她也用了好多年。」
遲遲得不到晉升,林文文也嘗試在公司內部轉崗。在一次面試中,面試官問她:「你覺得男生寫代碼跟女生寫代碼有什麼不一樣?」
林文文懵了,她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都是寫代碼,能有什麼不一樣?」
面試到最後,她越想越不舒服。兩人鬧得很僵,面試自然也失敗了。
外界對於女程序員有這樣一個誤區,認為她們會被「眾星拱月」般捧着,最苦最累的工作都由男生來干。但林文文覺得:「最重要的活兒一定是最累的,這不叫優待,我認為的優待反而是認可、器重,而不是只交給你非常輕鬆的活兒。」
在公司3年,林文文更多擔任執行者的角色,而非真正決定技術方案的核心成員。
在大廠,她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工作好像不是寫代碼。「技術方案上我從來沒有什麼話語權,像年會、聚餐、團建、經費這類事情倒是會第一時間想起我。」林文文說。一旦她拒絕,領導就會把類似的工作交給更年輕的女性員工。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孫萍從2016年開始關注女性程序員的職場困境。
她在研究中發現,程序員的考核是「技術至上」的。女程序員因為在語言交流方面的優勢,通常會接管和負責溝通、會議組織等工作。但是,這些非物質勞動在實際工作考評中所占權重不高,而且會被標記為「非核心類」工作。
林文文意識到,女性身份在職業發展中可能是個阻礙。她回想,自己在參與評審時,評委都是男性,做出公司重大決策的總經理辦公室成員也都是男性。
目前,互聯網公司的女性高管大多集中在相對「守業」的職能線,像法務、人力資源、財務等,並非業務條線,技術女高管更是少之又少。
科銳國際互聯網行業總監黃旭洋估算,決策層中女性比例在20%以下,技術崗位的女性高管不超過5%。
他形容這就像一個漏斗。首先,學習計算機專業的女生本來就比男生少;其次,在互聯網行業,抗壓能力和投入度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標準,而受文化、家庭、婚育等因素影響,選擇這份工作的女性較少;最後,要往更高級別晉升,不僅要考驗技術能力、管理能力,還要有很好的商業意識,而這非常取決於是否能晉升到中層,積累足夠多的經驗。
年齡、生育與母職
「一切都合法合規,你挑不出來任何問題。」林文文覺得,老闆最喜歡的就是剛當爸爸的男同事,他們要拼命賺錢養家,如果一個男生在30歲遲遲得不到晉升,可能立馬就跳槽了,「公司在賭」,一個30歲上下、面臨婚期與孕期的女性會選擇穩定而非跳槽。
去年9月,剃刀在豆瓣發起「Women In Tech女性科技從業者集合地」小組,一年時間吸引了超過37000名「科技姐妹」。
小組成員超過37000人管理小組一年,剃刀見過最多的煩惱都跟年齡有關。她經常看到有人發帖說「大齡女轉碼」,點開一看,才二十七八歲。她開玩笑說:「20多歲都叫『大齡』了,那30歲是不是要『入土』了?」
孫萍對比了中印兩國女程序員的職業發展,發現中國女程序員對職業發展有更強的周期焦慮感,認為「短線拼時間,長線不看好」。
馬上30歲的林文文要結婚了。她是女同學中第一個步入婚姻的,而身邊的男同事、男同學們很少有拖到現在的。「(女程序員)都是在透支自己,如果想備婚、備孕,其實就不能透支到120%了。」
長時間的高壓工作,林文文覺得自己身體和精力都不在最佳的狀態,她和先生暫時沒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如果能再來一次,她希望自己能早一點生孩子。
穆穆之前是一家外企在中國的軟件工程師,完成了團隊從1到20人的組建。懷孕期間,半夜爬起來和美國總部開會是常事,她形容自己「比較皮實」,一直工作到預產期前兩三天。
即使是「皮實」如穆穆,生完孩子以後,她患上產後抑鬱,整宿整宿不願意睡覺。
後來,她明顯感覺自己的精力在下降。以前讀書的時候,她連軸轉一樣參加各類大賽,跟着導師做項目,「我只要通宵兩三天肯定解決掉」。現在,一次熬夜需要花一個星期才能恢復。
「以前好像充電10分鐘能奮鬥一整天,現在是耗電10分鐘、充電一整天。」穆穆說。
孫萍指出,中國互聯網騰飛只有短短20年,需要大量、高速地消耗勞動力。「整個經濟的發展像大熔爐,我們就是一根根的柴火,什麼樣的柴火更耐燒、燒的時間更長,這是它最關心的。」
孫萍承認,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工賦予女性很多工作之外的事情,高強度、高壓力的「996」工作制使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難度凸顯,這個時候,女性程序員在性別上確實存在劣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每天男性用於家務勞動、育兒等無償勞動的平均時間為1小時32分鐘,女性為3小時48分鐘,是男性的2倍多。
分城鄉、分性別的居民無酬勞動時間情況有這樣一個段子,大廠做到P9的程序媛有三類:一是孤獨終老,二是丁克,三是有孩子還能做到不睡覺的。
即使是丁克,跳槽升職之路也不輕鬆。
楠楠之前是一家小公司的程序員,但過了30歲,老闆經常旁敲側擊地跟她說:「女性過了三十就應該輕鬆坐辦公室。」
不到半年時間,楠楠從開發調到測試,又調到產品,離一線研發崗位越來越遠,甚至連人事都告訴她:「這就是明升實降,薪資不會再有更高的變動了,甚至可能會隨着崗位調整降低。」
於是她離開了這家公司。辭職後,她在面試中總會被問到婚育問題,尤其是大企業,儘管她強調自己是丁克,但對方總會以「不相信會丁克,隨時都可能生孩子」為理由拒絕她。
黃旭洋指出,目前互聯網行業是一個「吃青春飯」的行業,25~35歲是中流砥柱,女性的婚育年齡正好與職業上升期重合。
「互聯網公司的成長速度非常快,在後備人才充足的大廠,當女性31~32歲再回到職場的時候,可能原來的下屬都已經衝上來了,這個時候就很尷尬。」重返職場的女性,要麼接受這樣的尷尬局面,在原公司接着幹下去,要麼只能換公司、換賽道、換環境。
京東副總裁杜爽向劉強東坦白自己懷孕「成為」男性
在這樣的職場生存下去,法則是把自己「活成」男性。
上大學的時候,林文文所在班級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直到走上工作崗位,她才意識到這一行的男女比例有多懸殊。她目前所在的小組有30人,只有3名正職的女程序員,男女比例達9﹕1。
根據獵聘發布的《2020程序員人才大數據洞察報告》,程序員男女比例接近8﹕2。
圖源《2020程序員人才大數據洞察報告》即使是美國,數字也是相似的,科技領域的女性從業者只占26%,其中7%是亞裔。
剃刀是在美國讀的大學。「大部分時候,你都是孤身一人的。」比如要完成小組作業,男生要麼覺得女生不太行,要麼不知道如何跟女生相處。「男生和男生之間總有一種兄弟文化,女生只能找女生組隊。」
工作以後,這樣的兄弟文化同樣存在。同事之間閒聊,球賽是男同事們最常提起的話題。「作為一個女生,如果不喜歡球賽的話,你往那兒一站就有點尷尬。但也從來沒有男生說,有女生在,要不要聊點別的。」
林文文與男同事的話題一般也圍繞着工作、遊戲,「聊他們喜歡的東西」。事實上,她還喜歡看書、看電影,卻從來沒有跟男同事提起過。
更有甚者,男同事們偶爾還會說起黃色笑話,令在場的女同事十分尷尬。
女程序員在技術分享中感到不適格子衫、拖鞋、宅男、悶騷、不修邊幅……對程序員工作的想象是依據男性生活經驗描摹出來的。
「生活在這一群人中,好像也沒有什麼打扮的動力。」林文文早就不關心最新的口紅色號,就算是周末也很少打扮自己。「可能我也被『男性化』了吧。」
美國學者坎迪斯·韋斯特和唐·齊默爾曼提出「做性別」(doing gender)的理論,指出性別是社會互動的產物,人會在日常行為與人際互動中,按照社會所期待的性別意識形態行動。
孫萍發現,女性程序員為了融入程序員群體,試圖淡化自身性彆氣質,模糊「男性」和「女性」的社會界線,來讓自己的性別身份「合法化」。
作為女程序員,要想一路「打怪升級」,成為技術崗位的領導者,讓自己「成為」男性,似乎是一條必經之路。
剃刀觀察,很多女性高管都要比同級的男性高管更強勢,作為領導的女性有時候「左右不是人」。一方面,她們要表現得比男同事更加堅強、果斷、「不好惹」,才能讓人覺得她專業、有能力。
另一方面,如果太強勢,又會被人說不好相處。「對女性有一種刻板印象,就覺得女生應該是軟軟的、比較好合作的。」
工作六年,林文文只在技術崗位上遇到過一位女性項目經理。
她給林文文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一次,林文文偶然看到這位經理入職時的工卡照,眉清目秀、化着淡妝。而當林文文認識她的時候,她穿着衛衣、馬甲,頭髮簡單扎在腦後,沒有什麼打扮,跟溫柔完全沾不上邊,「感覺變了一個人」。
和這位領導共事的那段時間,也是林文文工作以來加班最狠的一段時間。發布、上線、驗證,每天上班都到次日凌晨一兩點才能下班。
當時,女領導離預產期只有不到一個月。她不僅和大家一起加班,還在大家下班之後一個人留在公司,盯着項目上線後沒問題才能放心。女領導一直工作到預產期前一天,產假也少休了一個月。
男性與技術「合謀」,女性與自我和解
「男性氣質是刻在技術的DNA里的。」孫萍在研究中指出,男性與技術組成一種「合謀」,這種「合謀」與教育話語、技術發展、性別分工等社會結構密不可分。
她指出,無論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化時期,技術的發展都與社會生產、軍事活動息息相關,男性在這些領域都占據主導地位。
「當男性在技術框架中占主導地位,女性很難被寫進歷史。」孫萍介紹,鮮有人知道,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員阿達·洛夫萊斯(Ada Lovelace)是一位女性;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ENIAC背後有一支由6位女性組成的團隊,完成開創性的編程工作,但她們只能被稱作「計數員」而非「科學家」。
在微觀層面,家庭的養育也影響着技術朝着社會既定的性別規範發展。孫萍舉例,從小給男孩子買槍、買坦克、買遊戲機,給女孩子買洋娃娃。女性被培養成一個好學、努力、聽話的人,但男性是冒險、勇於嘗試的,與編程所強調的探索、試錯精神一致。
這些性別問題會映射在產品上,轉化成對女性的忽視甚至物化、凝視。
「帶有一定特質的性別組群沒有參與到產品的研發中,它的性別特質也不會反映在這個產品當中。」 孫萍舉例,和白人和黑人男性相比,美國等國家警方所使用的Idemia人臉識別系統更容易混淆黑人女性。
黃旭洋認為,從企業層面上看,技術崗位管理層男多女少的現狀,也會直接影響到團隊管理的人文關懷;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溝通能力、親和力成為對管理層越來越重要的考量,在這個層面,女性要比男性更好一些。
在黃旭洋看來,只有當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公司更加核心的業務領域中,介入更有影響力的決策層,才能對目前的局面有所改變。
發起「Women In Tech」豆瓣小組的剃刀就帶着這樣的期待。
在美國找工作的時候,剃刀參與了Grace Hopper Celebration(GHC),這是為了紀念軟件工程師、編譯語言之母Grace Hopper而設立的女性科技從業者聚會,同時也是一場面向女程序員的招聘會。
在GHC上,剃刀看到前輩是如何在這個行業生存下來的,強烈地感受到「自己不是一個人」。
「女生之間這種互助的關係真的非常寶貴。」剃刀也想把這樣的感受帶給其他女性同行。
在「Women In Tech」豆瓣小組裡,大家互相鼓勵,分享經驗。困擾「科技姐妹」們的問題可以很大,比如如何補齊短板、該不該轉崗或跳槽,也可能很小,比如簡歷上應不應該標上性別。
小組過往舉辦的分享會剃刀發現,組裡的姐妹們特別容易自我懷疑,「就像楊笠在段子裡說的那樣,考了70分,就覺得自己是不是不適合這個學科」。這種時候,剃刀就會在回覆中分享自己剛開始學代碼時的崩潰經歷。
她希望,能營造一種向上的氛圍,就算是學得一般的女生,也能在這個學科找到自己喜歡的點,行業里的女性也能慢慢多起來。
穆穆覺得,自己走上程序員這條路,和不遺餘力支持她、願意傾囊相授的老師們密不可分。
從三年級開始, 當其他小朋友都在學樂器的時候,穆穆就坐在了學校機房的電腦前。當年,計算機普遍使用的還是DOS系統,穆穆從學打字開始,逐漸接觸了Basic語言、foxpro語言、3D Max動畫製作。
初二那年,穆穆在每天晚自習下課後,都會和另一個好朋友騎着自行車,從北到南穿越縣城,去老師家補習計算機二級考試。在小小的工廠宿舍里,穆穆與代碼結下近30年的不解之緣。
孫萍和黃旭洋都認為,短時間內,男性主導的情況得不到改變。在暫時無解的現狀下,女程序員們開始積極向內和解、改變自己。
晉升受阻的林文文在考慮跳出大廠,不再寄希望於老闆的「下次一定」。30歲、未婚未育兩個標籤讓自己自帶篩選企業文化性別平等的buff,如果被問到婚育問題,那就是彼此之間需求不契合。「沒必要非往上湊,想用一己之力去改變規則,自己太累了。」
走出產後抑鬱的穆穆選擇自己創業,轉型做了全棧,偶爾接一些外包項目,做過視頻互動課程、產後修復、在線婚戀交友、兒童編程等多個創業項目。
但人數的增長必然帶來職場平等嗎?
「在我們的認知里,社會框架好像都是在依據數量,數量會形成力量,然後形成影響力。」但孫萍覺得,話語權不應該由人數多少來決定,而是應該呼籲一種新的生存和發展的框架。「公平不是多和少,是每一個個體都很重要的理念。」
(林文文、剃刀、楠楠、穆穆為化名)
(編輯:黃玉璐 校對:顏京寧)
參考文獻:
[1] 孫萍 . 技術、性別與身份認同——IT 女性程序員的性別邊界協商[J]. 社會學評論,2019(3):71-83
[2] 孫萍.性別的技術政治——中印「程序媛」的數字勞動比較研究[J].全球傳媒學刊,2021,8(01):93-107.
[3] Sun P . Straddling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the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female programmers in China[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9(1):1-16.
[4]蔡玲. 科技職場中女性的職業處境與性別管理——以IT女性程序員為例的質性分析[J]. 青年探索, 2020(5):7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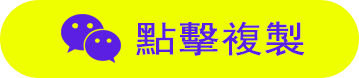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確實不錯,挽回了不少瀕臨離婚的家庭!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