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我們,不管男性還是女性,醒着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辦公室中度過的。上班族典型的一天是這樣的:早上坐很久的車通勤,來到某座大城市某個主要商業街區某棟摩天大樓的某張辦公桌前,坐下開始一天的工作......以工作謀生的我們,如何在辦公室隔間裡,獲取人生的自由?
我們習以為常的、朝九晚五的辦公室生活,是從19世紀末期才逐漸興起的。而自誕生起,它便同時開始了進化的旅程:從狹小的格子間到開放式的辦公區,再到如今流行的soho辦公、共享辦公,辦公空間的變化,似乎也讓朝九晚五的生活變得開闊了些。

但所謂「知識工人」真的擺脫了隔間,過上了擺脫辦公室束縛的生活嗎?我們今天想通過一本新出版的書《隔間》,跟大家聊一聊犀利、有趣的辦公室進化史;並且跟大家探討,「辦公室」在不遠的未來是否可能走向真正的自由?
每個打工者心裡
都藏了一個「打砸辦公室」的夢
我們一起來想象一段監控影像。
在一個個辦公格子間,辦公室職員們一個個窩在一間間由日光燈照明的小隔間裡,眼睛緊盯着電腦屏幕。一名身着襯衫、打着領帶的男子坐在辦公桌前,旁邊是他的同事,蜷縮在文件櫃前翻找文件。突然間,這名坐着的男子抓起一摞文件,用力扔向他的同事。隨後,他舉起桌上的電腦,砸向另一張辦公桌。隨後這名男子拿起辦公用的紙張,向遠處呆若木雞的同事們瞄準,將這些紙甩向他們。躲在角落裡的兩名同事用手機錄着這名男子的行為。男子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滿身怒氣,他從一張桌子後抓起一根大棍子,開始砸向複印機......
這段監控影像經網友分享後,在知名科技博客Gizmodo病毒式傳播開來。評論如潮水般湧來,人們迫不及待地表達對這名「打砸辦公室」男子的欽佩與理解。「這哥們太酷了。」「他真正懂得什麼叫活着。他的那幫獄友真該一同加入這場反抗。」後來,如同很多爆紅的事件一樣,當這個視頻點擊量超過幾百萬時,有人出來說視頻是偽造的。但不管這個視頻是真是假,它確實戳到了人們的痛處。不管人們覺得這視頻是真的還是偽造的,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內心深處,每一個打工者都希望這視頻是真的」。這種願望,從「打砸辦公室」為主題的手遊的流行程度,就可窺見一斑。
遊戲《打砸辦公室》(Smash the Office)界面。
1997年,有辦公家具生產商(Steelcase Corporation )對格子間裡的辦公者們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93%的人想要換個工作環境。到了2013年,悉尼大學兩名研究者的調查結果顯示,情況在這些年中並未有過什麼變化:在全部的辦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間辦公者(人數大概是辦公室工作者的60% )對自身工作環境最為不滿;不出所料,獨立辦公室內工作的辦公者是這些人中對工作環境最為滿意的。
多年來,這股對辦公空間和辦公生活的不滿已經滲入了更廣泛的文化範疇。在電影《辦公空間》( Office Space,又譯《上班一條蟲》 )中,某家科技公司里怒氣沖沖的三人小團體將他們對公司裁員的不滿發泄到了辦公室的打印機身上。他們對打印機棒打腳踢——你可以在網上找到許多類似的模仿視頻。 在埃德·帕克的《個人時間》和約書亞·費里斯(Joshua Ferris )的《我們走到了盡頭》這兩本小說中,對電子郵件撰寫禮儀的討論成了一種准學術性的話題;發現早餐會議時還有剩餘的免費百吉餅可以吃,是辦公日常生活里的亮點。兩本小說都用了不帶感情色彩的「我們」來進行敘述,更好地傳遞出了當代白領生活圖景中消極的一致性和冷淡的無名感。而丹麥作家克里斯蒂安·雲格森(Christian Jungersen )的全球暢銷書《例外》則將「辦公室政治」的概念用到了極致。書中,辦公者互相鈎心鬥角,甚至互相殘殺。
職場諷刺漫畫《呆伯特》。圖中情節為呆伯特在隔間中聽到隔壁同事不停吹口哨,他不想發生衝突但又想表達不滿。思前想後,最終卻還是以向同事大喊大叫(「別再吹了,你個白痴!」)而告終。
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漫畫《呆伯特》(Dilbert )。《呆伯特》將辦公室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無趣和無聊變成了簡潔明了便於攜帶的諷刺作品。後來這漫畫能發展出了各種周邊產品:呆伯特桌面日曆、呆伯特馬克杯、呆伯特鼠標墊和呆伯特毛絨玩具在辦公室里隨處可見。而這種千篇一律、恆久不變,正是漫畫《呆伯特》擅長諷刺的對象。儘管《呆伯特》有時候陰鬱黯淡,但是翻看整部漫畫是一種簡單甚至人文的體驗。這種感覺被電影《辦公空間》裡的一個角色用非常簡單的話描述了出來:「人被生下來,並不是為了待在狹小的隔間內,對着計算機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
或者你可以化用盧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隔間之中。
辦公室進化史
從隔間到「開放式」辦公區
巴爾扎克說過「幸福沒有歷史」,辦公室也沒有。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說:「白領躡手躡腳地來到了這個世界。」白領工作的地方也同樣悄無聲息。而其他諸如工廠等工作場所,來到世界的時候可是伴隨着咣當聲和鳴笛聲的,動靜頗大;獨獨辦公室毫無聲響。到了20世紀中期,也就是米爾斯寫作《白領》這本書的時候,辦公室里的男男女女幾乎是美國勞動力市場中最大的組成部分。然而,辦公室到底從哪裡而來,這依然是一個謎。或許是太乏味平常了吧,所以大家都覺得沒什麼好認真研究的。
《白領》
作者: [美] C.賴特·米爾斯
譯者: 周曉虹
版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人們是在19世紀中期注意到了辦公室的概念。最初這些地方被稱作賬房,跟幾百年前意大利經貿商人的辦公室沒什麼區別。這些地方小而舒適,或者起碼是小的吧。人們意氣風發地來到這裡工作,等到走出這油箱般的地方時,早已佝僂萎縮。在這油箱般的地方,那麼多的勞動卻好像只生產出了文件。
商貿是高貴的,驚險刺激:它帶領人們走向富貴繁榮。然而辦公室卻是虛弱空洞的,最重要的是,還很無聊。然而正是這份無聊和令人乏味的體面感,使得辦公室成為20世紀一大不可或缺的話題基礎:各種關於中產階級的美言,各種關於穩步向上爬升的職業承諾。這個陰暗小房間裡的小小辦事員說不定有一天就登上了人生巔峰;這窩在雜亂賬房裡的小小會計,今天還在這裡處理着各種數字,明天說不定就在勇氣的帶領下成了CEO;待在格子間的碼農說不定就一路碼進了董事會。不論出現怎樣的變遷,辦公室帶給人們對於職業發展的持續希望,和對穩定體面生活的保證,是其他任何工作場所都無法企及的。
電影《玩樂時間》劇照(雅克·塔蒂,1967 ),展現了一幅早期辦公室隔間的經典圖景。
換句話說,辦公室不該是無聊的代表。事實上,自20世紀初期,辦公室就成了美國職業生活方面最具烏托邦精神的理念與情感的策源地之一。辦公室開始從最初的模樣擴大成為鍍金時代(Gilded Age,處於美國南北戰爭和進步時代之間,時間上大概是1877年到1893年,是美國財富突飛猛進的時期)龐大繁華生意的行政中心。彼時,辦公室為人們提供了從另一個無聊乏味的代表場所——工廠——逃離的可能。具有遠見卓識的建築師設計出了辦公大樓。這些大樓內部規整高效,有如生產流水線,只不過少了身體上的危險和辛勞,也因此更能體現出社會威望。到了1950年代,職場新人男孩(也可能是新人女孩,雖然概率小許多 )已經可以在腦海中想象自己一步步攀爬職業階梯的畫面。在這畫面中,他或者她手中的權力不斷增大,底下供其使喚的部屬不斷增加。
不同時期、不同影視劇中對辦公室的布景,從中可以看到,人們對辦公室的要求越來越看重開放性與舒適性。
20世紀中期的美國,白領工人所獲得的威望和象徵的權力是其他工作所不能提供和賦予的。而一些白領工人身居的場所,也成為20世紀最具標誌性的建築。到了1960年代,管理學理論家們開始暢想一個新的辦公室工作群體,即計算機科技發展下的「知識工作者」:這些白領受過良好教育,是具備創新能力的職業人,他們用「思考能力」來換取報酬。辦公室空間開始出現形式上的變化,辦公室設計理論家為這群「知識工作者」設計出了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辦公室布局。1990年代,隨着互聯網泡沫帶來的狂熱幻想,各種烏托邦式辦公空間更是源源不斷出現:仿若微型城市一般的辦公場所,有着保齡球場地的辦公場所,堪比大學校園的辦公園區,猶如布置過的家庭車庫或娛樂室的小而舒適的辦公室。
隨着21世紀初期遠程辦公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設計師和理論家開始瞥見實體辦公室的終點。實體辦公室將被隱形而又無處不在的、坐在咖啡館和起居室里、連着互聯網的辦公群體所取代。一家名義上位於印度孟買的公司,員工可能在美國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待着,穿着睡衣睡褲就可以參加公司的網絡會議。
辦公室的未來
形式更自由,但人們尚未真正擁有「自主權」
然而拉近了看,就會發現畫面並沒有那麼美好。
照搬工廠車間的模式,使得辦公室工作也變成了麻木的重複性勞作。20世紀中期的中層管理者感到自己的精神被上了枷鎖,成了一個「組織人」,靈魂被公司俘虜了。女性進入白領階層之後,則往往被分配到行政或秘書方面的崗位,這就很難往上升職,並且還飽受性騷擾的困擾,陷入了一種雙重的附屬境地。辦公場所本身則遭到了無窮無盡的複製,內部裝修缺少人性溫暖。
人們試圖修復這些問題卻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德國時髦的開放式「辦公室景觀」造成了亂糟糟的工作環境,讓人無法專注工作;互聯網公司瘋狂的辦公室之所以被人們銘記,不是因為理想主義的設計風格,而是公司員工們瘋狂的工作時長——許多人都稱它們為「白領血汗工廠」。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人成了在咖啡館裡工作的自由職業者,但隨之而來的還有財務上的持續不穩定,沒有福利,且相對來講在工作過程中缺乏社交。簡而言之,白領的故事就是有關自由和升遷承諾的故事,只不過這自由和升遷的承諾一次又一次地沒被兌現。
《白領》出版於1951年,當時白領工人在勞動力市場占比幾乎達到50%。大部分觀察家都認為這個新興群體將要代替由工匠和個體商人組成的舊有中產階級。米爾斯的描繪很不留情:他眼中的白領就是些「小男人」,是自主的追隨者,他們覺得自己獨立自主、具備創業精神,哪怕身陷大公司的牢籠。儘管他們的工作逐漸變得和工廠工作一樣——日復一日,但是這份職業中一些無形的威望和地位讓他們察覺不到。按米爾斯的說法,似乎整個白領階層都可以被視作新中產階級,因此是一個獨立的群體。
儘管「白領」工作逐漸變得跟「藍領」工作一樣——日復一日,但是這份職業中一些無形的威望和地位讓他們察覺不到。
然而縱觀辦公工作的歷史,其所體現出來的並非如此。辦公室內的事情也好,辦公室外的事情也罷,鮮少是穩定不變的。而辦公者對自身的理解,對他們生命際遇的理解更是變幻莫測。
眼下,儘管有些大公司已經採用聯合辦公的空間共享方式,但對此現象表現出興趣的群體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還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不過這部分人群預計還會增加。據軟件公司財捷集團(Intuit )預測,至2020年,自由職業者、臨時雇員、日薪工、獨立承包商將占到勞動力市場的40%;根據格林沃爾德的計算,這部分數字甚至可能達到50%。而就算是50%,都有可能低估了這個國家將要面對的臨時勞動者的數量。這些臨時勞動者當然不會全是辦公室員工。但似乎辦公室員工中的很大一部分將要走向自由職業,或者起碼說會有很多時間投入到自由職業的工作中。
電影《她》中的辦公空間,具備個性化、暖色調的裝飾風格,並更加注重開闊性與舒適性。
說到這裡,關於「自主權」的問題又重回我們的視線。在永久雇員眼中,自由職業者和臨時雇員或許看起來享有更多的自主: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從事什麼樣的工作(自由職業者),或者他們可以決定合同的期限長短(臨時雇員 )。然而除此之外,非永久雇員怕是很難再提出其他方面的要求了。眾所周知,自由職業合約的執行是很困難的;勞動力市場越自由,公司對雇員的掌控也就越強。根據「自由職業者聯盟」這個幫助獨立承包商獲得健康福利和其他保障的組織的調查,超過77%的自由職業者在人生中的某個時刻經歷過「討薪難」的煩惱。自由職業者和其他非正式雇用工的數量或許被低估了,
從這方面而言,我們正在重返前工業化時代,以一種不同的路數。回看19世紀中期,彼時的勞動力市場廣闊且未受管控,工作者的數量也並未經過任何系統的測算。隨着不穩定雇員的增加,以及永久雇員境況不穩定性的增加,工作的形態似乎是在往回退而不是往前走:正在重返那個更早的不安的時代。因此,辦公室本身或許正逐漸消失,或者起碼說正在退回到20世紀初它剛剛誕生時的那個模樣,也就不那麼偶然了。
靈活性不會是管理手冊上新增加的用來讓員工服服帖帖的把戲。靈活性,就像科技一樣,是一種工具,一個機會:它就在那裡等待着,等待着人們去拿起來享用。辦公者願意拋棄辦公桌和辦公室這些象徵身份地位的東西,不僅僅體現出管理層對經費控制的需求,也暗示着,定義了幾代白領人的職業路徑——從格子間到角落辦公室,從秘書池到沿着通道來回走動巡視——已走向尾聲,而另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儘管還未完全成形,已將其取代。最後,就看辦公者是否能賦予這份自由真正的意義:看看他們是否能把勞工合同打磨成切實有效的合同,看看他們是否能將這份「自主權」行使得真實可靠,看看他們是否能讓辦公空間真正屬於他們自己。
《隔間》
作者: [美] 尼基爾薩瓦爾
譯者: 呂宇珺 版本: 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5月
本文系獨家內容。整合自」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隔間》一書開篇及第2、4、6、9章內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較原書有刪節及調整,內容經出版方授權刊發。作者:尼基爾薩瓦爾;譯者:呂宇珺 ;整合與編輯:走走。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所謂白領,是為了體面生活不得不放棄其他追求的人們
「葛優躺」,我們抵抗時代的稻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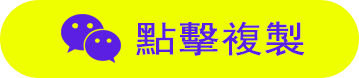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有時侯自己陷進去出不了只能找專業的人士幫忙,我覺得挺不錯的,推薦!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
被拉黑了,還有希望麼?